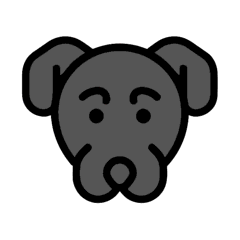格琳童袜Ⅰ——🧦卖袜子的小女孩🧦(更至 平安夜 PM11:05)
搞笑灵异萝莉纯爱NTR小男孩M榨精足交踩踏贡奴
🧦🧦🧦圣诞快乐
我是格琳,喵——
我年轻那阵,还有完整九条命的时候,曾经是只到处旅行的菲琳(菲琳,学名“菲琳涅尔”,就是人类俗称的“猫娘”)。只剩一条命后,我放弃了冒险生涯,转而找了份安稳的工作——『欲都』烛圣所书库的管理员。我的同事们喜欢叫我“书匠”,大概是因为我常在空闲时候写书偷偷塞进书架吧……
今天整理旧物时,翻到了这本——啊哈!《格琳童袜》,它是我周游『背德地狱』期间写下的童话集。说是“童话”可能不太准确,地狱哪有什么纯洁的儿童故事,这些都是我在旅途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自参与……咳咳,开玩笑的,没有亲自参与。我又不是那群离了精液不能活的『三途川婬普』……(这么写不会被『幼天使』给审查掉吧?)
总之都是能溯及源头的故事。当然,我加入了一些合理的艺术改编,真正的『背德地狱』可比童话里更光怪陆离。
那我为什么最终敲定了“童袜”这个替代词呢?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太棒了,每篇故事都像一双孩童的袜子,有轻巧可爱的外表,内里却藏着走路磨出的线头,还有那些只有穿袜女孩子才知道的,脚趾缝里的秘密……
行了,这些话就当作前言写在开头好了。闲话少说,来吧,我这里正好有一杯凉透的热可可,有一张沾满橘猫毛的软垫子,还有一整个『尖昼』的摸鱼时间。
——那么,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我是格琳,喵——
我年轻那阵,还有完整九条命的时候,曾经是只到处旅行的菲琳(菲琳,学名“菲琳涅尔”,就是人类俗称的“猫娘”)。只剩一条命后,我放弃了冒险生涯,转而找了份安稳的工作——『欲都』烛圣所书库的管理员。我的同事们喜欢叫我“书匠”,大概是因为我常在空闲时候写书偷偷塞进书架吧……
今天整理旧物时,翻到了这本——啊哈!《格琳童袜》,它是我周游『背德地狱』期间写下的童话集。说是“童话”可能不太准确,地狱哪有什么纯洁的儿童故事,这些都是我在旅途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自参与……咳咳,开玩笑的,没有亲自参与。我又不是那群离了精液不能活的『三途川婬普』……(这么写不会被『幼天使』给审查掉吧?)
总之都是能溯及源头的故事。当然,我加入了一些合理的艺术改编,真正的『背德地狱』可比童话里更光怪陆离。
那我为什么最终敲定了“童袜”这个替代词呢?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太棒了,每篇故事都像一双孩童的袜子,有轻巧可爱的外表,内里却藏着走路磨出的线头,还有那些只有穿袜女孩子才知道的,脚趾缝里的秘密……
行了,这些话就当作前言写在开头好了。闲话少说,来吧,我这里正好有一杯凉透的热可可,有一张沾满橘猫毛的软垫子,还有一整个『尖昼』的摸鱼时间。
——那么,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卖袜子的小女孩🧦
平安夜 PM10:47
上帝在自己的生日不好好唱生日歌吃蛋糕,反倒在对流层鼓捣起祂那台碎纸机。雪梨纸做的云层纷纷被搅碎,雪花簌簌落下。
一个名叫莉瓦的孩子,此刻蜷在街边的垃圾桶旁,身上只披了件火红的旧风衣,光溜溜的腿从衣摆下伸出来,冻得通红。脚上?没穿鞋,只有一双薄薄的白色短袜。
她面前摆着三双袜子。
左边那双是华丽的深蓝色长筒袜,袜口有一圈星星点点的假水晶装饰。中间那双是红白条纹的及膝袜,厚厚羊毛材质。右边那双则是普通的灰色中筒棉袜。
第一个顾客来得比她预想的早。
玛蒂尔德从店铺的余温中走出时,她的脚踝正处于高跟鞋的谋杀进程中。一套新买的深蓝色蕾丝内衣还躺在她提包里——她准备给丈夫一个惊喜。
然后她看见了莉瓦。
「天哪,这怎么有个孩子!」玛蒂尔德提着皮草外套蹲下来,「这么冷的晚上,你怎么坐在这里?你父母呢?」
莉瓦抬起脸:「爸爸说……说要卖掉这些袜子才能回家。」她指了指面前的三双袜子,「姐姐,买一双吧?很暖和的。」
玛蒂尔德的视线立刻落在左边那双深蓝色长筒袜上:「这双……真漂亮,这是什么面料……」她喃喃道,抚过天鹅绒丝袜表面,「正好配我刚买的……」
「是很少见的名贵料子。穿上它的话,您丈夫一定会印象深刻。」
没有过多犹豫,这场交易以二十克朗达成。玛蒂尔德把袜子塞进提包,匆匆走向一栋暖黄色窗户的房子。
平安夜 PM10:47
上帝在自己的生日不好好唱生日歌吃蛋糕,反倒在对流层鼓捣起祂那台碎纸机。雪梨纸做的云层纷纷被搅碎,雪花簌簌落下。
一个名叫莉瓦的孩子,此刻蜷在街边的垃圾桶旁,身上只披了件火红的旧风衣,光溜溜的腿从衣摆下伸出来,冻得通红。脚上?没穿鞋,只有一双薄薄的白色短袜。
她面前摆着三双袜子。
左边那双是华丽的深蓝色长筒袜,袜口有一圈星星点点的假水晶装饰。中间那双是红白条纹的及膝袜,厚厚羊毛材质。右边那双则是普通的灰色中筒棉袜。
第一个顾客来得比她预想的早。
玛蒂尔德从店铺的余温中走出时,她的脚踝正处于高跟鞋的谋杀进程中。一套新买的深蓝色蕾丝内衣还躺在她提包里——她准备给丈夫一个惊喜。
然后她看见了莉瓦。
「天哪,这怎么有个孩子!」玛蒂尔德提着皮草外套蹲下来,「这么冷的晚上,你怎么坐在这里?你父母呢?」
莉瓦抬起脸:「爸爸说……说要卖掉这些袜子才能回家。」她指了指面前的三双袜子,「姐姐,买一双吧?很暖和的。」
玛蒂尔德的视线立刻落在左边那双深蓝色长筒袜上:「这双……真漂亮,这是什么面料……」她喃喃道,抚过天鹅绒丝袜表面,「正好配我刚买的……」
「是很少见的名贵料子。穿上它的话,您丈夫一定会印象深刻。」
没有过多犹豫,这场交易以二十克朗达成。玛蒂尔德把袜子塞进提包,匆匆走向一栋暖黄色窗户的房子。
新系列,好耶
平安夜 10:48
助理医师拉斯马斯的平安夜值班结束后,走进这家离医院不远的鲱鱼酒馆,
今天酒馆里人很少。拉斯马斯在吧台坐下,准备脱下还沾着雪的外套。当他把胳膊抽出袖子时,他看见了那个孩子。
她坐在角落的高脚凳上,双腿悬空,红色圣诞裙摆下是粉色长袜和漆皮小皮鞋。一顶毛茸茸的红色圣诞帽歪戴头上,其下是两条精心编结的淡金色双马尾。她面前摆着三只倒扣的锡杯。
「老板,」拉斯马斯对酒保说,「怎么有个孩子……」
「哪个?」酒保头也不抬地擦着杯子。
「角落那个,穿圣诞老人装的那个。」
酒保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先生,那里没人。您是不是醉了?」
「醉了?我还没开始喝呢。」他小声嘟囔。
「拉斯马斯先生,」女孩反倒朝他招了招手,「要玩个游戏吗?」
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难道是同事或者朋友的孩子?拉斯拉马心想。
「你是谁?我们认识吗?」
「你能赢下游戏的话,我自会告诉你。」
「好吧,什么游戏?」
「猜杯子。」她指着吧台上的三只锡杯,「现在中间这一只下面,藏着一颗能实现愿望的星星。接下来我会不断交换它们的位置,你猜星星在哪个杯子下。猜对了,星星归你。猜错了……您就付我一点“记忆”。」
哈哈,都什么跟什么,小孩子游戏。
拉斯马斯本该离开。但他刚结束一场八小时的手术,病人没能下手术台,血液与生命在手下流逝的空虚感此刻在指尖搏动。幻觉也好,恶作剧也罢,他需要一点别的东西来覆盖那段记忆。
「好。我玩。」拉斯马斯坐到女孩身边。
「那么,游戏开始咯。请看好。」
她没有像街头骗术那样快速移动杯子,反而极优雅地将它们扣着滑行,杯脚与木质台面缓缓摩擦。
「停。」 女孩双手离开杯子,乖巧地交叠在膝上。杯子静静立在那里,在吧台灯光下投出三个短短的影子,毫无分别。
拉斯马斯根本没注意看,随手指向中间的杯子。
「第一回就少取一些……」女孩脱掉皮鞋转向拉斯马斯,对他伸脚,「就取走您这次失败手术的记忆吧。」
「什么——」
女孩的粉袜脚掌踩上拉斯马斯的下体。
「你干什么——」拉斯马斯慌乱四下张望,寥寥两三个客人都专注于自己的酒杯,没有人在意这边发生了什么。女孩开始用脚隔着裤子揉搓着他的肉棒。
「你别胡闹了!」
女孩没有理睬,另一只脚也踩了上来,两只小脚灵活地在拉斯马斯裆部扭动。酥麻快感从裤子里蔓延开。
「唔呃呃……怎么会这么……舒服……」
没一会,他就在粉袜子的蹂躏下射出疲惫的精液。然而裤子并没被沾湿,果真如女孩所言,袜尖像是漩涡吸盘一样把精液连同他脑中的记忆片段尽数吞噬,只留下一腔记忆空洞。他忘了自己今晚在为谁动刀,忘了那具尸体的名字。今晚医疗事故的所有声音色彩细节都溶解进了女孩的脚底。
「您输了哦,拉斯马斯先生。不过,这下你该相信我的魔法了吧?」女孩收回双脚,「要继续吗?」
拉斯马斯还沉浸在射精与记忆抽取后的双重空虚中,茫然点头。直到女孩停止交换杯子,他才清醒过来,察觉不妙。
「我不玩了,我要走了!」
「不可以呢。」女孩脚一蹬椅子,飘落进斯马斯的怀里,轻轻揽住他的脖子,双脚直接探进他的裤腰带内,贴上肉棒,「中途离开游戏是犯规,犯规就要受罚。」
「你要干什么?!放开我!!」
「你看,你的小鸡鸡又硬起来了。它很喜欢我的脚呢,虽然只是小孩子的脚丫……但是我只要一按摩,它就会缠上我的脚。」女孩一边用双脚夹住拉斯马斯的肉棒上下撸动,一边坏笑,「来~让我听听,它到底在求什么……哦~原来你的小弟弟,想要再输一次呢~再让你输,再抽一次你的记忆,让他舒舒服服射精哦~」
「快停,快下来!不可以……」
「瞧~你的小弟弟在点头哦~看,它已经按耐不住了~」 女孩双脚加快了频率。
「这次是您去年平安夜,母亲给您织的新毛衣带来的温暖记忆。」女孩的手指轻点在他的太阳穴。
「呃啊啊啊啊啊啊——」
拉斯马斯第二波高潮来得更快,随着粉袜脚的蠕动,他再度败北。母爱与节日温馨融化在女孩的足底,而他对此一无所知。
「怎么样,还要再来么?」女孩松开拥抱。
拉斯马斯急切地往后挪动,大口喘气:「不要!我不想再玩了!」
「嘘,我没有在问您。您的小弟弟显然意犹未尽呢~」女孩调皮地说,「没关系~只要猜中一次,之前全部的失败都会补偿回来~」
只能陪她玩了吗?
女孩又交换了一遍三个锡杯位置。
这次拉斯马斯仔细盯着看着,轮到指认时,拉斯马斯选择左边那只锡杯:「我选左边这只!」
「看看是不是呢~」
女孩掀开左杯,是空的。
「我明明记得很清楚!」他说着就要伸手打开剩下的锡杯看个究竟。
「擅自触碰未选中的杯子也是犯规哦。双倍惩罚。」女孩又蹭到拉斯马斯身上,双脚再次探入裤裆,双手也攀上了他的两个乳头。「这次……索要的是您“面对血不晕眩的勇气”、“认出所有骨骼名称的知识”,嗯……“未来第一次主刀的成就感”也帮你预支了~」
「住手!那种记忆怎么能——」
「是呢,就是重要所以我才要把它偷走哦。」
「啊啊啊啊啊啊~~!」
当女孩的双脚覆上肉棒,乳头也遭到抓挠,快感与记忆绞在一起。失去这两样东西,身为外科医生的尊严、职业价值,拉斯马斯都会失去吧。他在恐惧与绝望中爆发,惨烈射精的同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真的开始离书本上的知识越来越远。
「你这个恶魔……!!」
「呵,您早该发现的。一个深夜酒馆里的红衣女童,不是恶魔还能是什么呢?但您还是决定来陪我玩了~」她晃了晃腿上的粉袜,其中传来精液吸收的咕噜声,「唯一的解释是,您是恋童癖,明知危险与不合理却屈服于欲望凑上来的恋童癖。而我袜子里都只是您这种劣等生物微不足道的记忆罢了~」
他的视线开始模糊。吧台对面的镜子里,他看见自己的眼睛渐渐失去光泽,肩膀微微垮塌。
「最后一轮,这次你可以选择离开,我不会拦你了,」女孩的声音从耳边传来,「如果猜对了,您之前输掉的一切记忆,我加倍偿还。」
拉斯马斯知道酒馆里有人,他有想过喊人求救,但是在小女孩脚下被欺辱榨精的事如果大声宣扬出来,不久坐实自己是个恋童癖了吗?那种事情一旦发生,他就没法作为正常人类生活下去了。只要不被其他人看到,说不定可以装作这一切都没发生,他至少还维持正常的助理医师生活。即使失去一些专业知识,日后重新学习也并非难事。
更何况……接连射精三次的痛苦之后,女孩的脚给他带来了奇妙的感受,他还想再体验一次。
拉斯马斯盯着女孩嘲弄的双眸。他的理性在尖叫,但内心深处传来一种自毁的冲动,一种想看看自己究竟能堕落到什么程度的病态好奇控制了他。
「……我继续。」
女孩微笑着伸出双手,再一次交换了那三个杯子的位置。
「我选中间。」
「哦呀?选这么快?最后一局了,不再考虑一下吗?」
「……。」
女孩轻轻抬起中央那只锡杯,下面只有一小块吧台木纹。
「彻底失败。」女孩趴进拉斯马斯怀里,双臂环抱住他的脖子,双脚夹住他的肉棒,「那么,把一切都给我吧,一切。您的知识、记忆、童年、爱情,除了关于我的记忆外,我都收下了。」
「等等……等等!你没说要……!」
「嗯?游戏之前我可是征得您同意了,取走什么记忆的选择权在我手里,您好像没什么资格阻止我呢~ 现在……让这双可爱的袜子成为您精液与灵魂的棺材吧~」女孩双脚发力,开始发狂研磨,十根脚趾紧紧夹住棒身,直接嵌进皮肉里。
「啊啊……」
「深~呼~吸~放~轻~松~把脑子清空~然后射出来啊~」
「啊……啊…啊……别……」
「很好~就是这样……来~给我的双脚,献上您全部的记忆吧~」
女孩用力一夹,拉斯马斯连续不断地射出精液,伴随着的是灵魂与记忆的大量流失。他就这样被女孩剥夺得一干二净。
圣诞女孩凭空消失,拉斯马斯重重倒在吧台上,昏睡过去。
酒馆外的街道上响起欢庆的圣诞歌,音乐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掩盖了刚才这出滑稽闹剧。
助理医师拉斯马斯的平安夜值班结束后,走进这家离医院不远的鲱鱼酒馆,
今天酒馆里人很少。拉斯马斯在吧台坐下,准备脱下还沾着雪的外套。当他把胳膊抽出袖子时,他看见了那个孩子。
她坐在角落的高脚凳上,双腿悬空,红色圣诞裙摆下是粉色长袜和漆皮小皮鞋。一顶毛茸茸的红色圣诞帽歪戴头上,其下是两条精心编结的淡金色双马尾。她面前摆着三只倒扣的锡杯。
「老板,」拉斯马斯对酒保说,「怎么有个孩子……」
「哪个?」酒保头也不抬地擦着杯子。
「角落那个,穿圣诞老人装的那个。」
酒保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先生,那里没人。您是不是醉了?」
「醉了?我还没开始喝呢。」他小声嘟囔。
「拉斯马斯先生,」女孩反倒朝他招了招手,「要玩个游戏吗?」
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难道是同事或者朋友的孩子?拉斯拉马心想。
「你是谁?我们认识吗?」
「你能赢下游戏的话,我自会告诉你。」
「好吧,什么游戏?」
「猜杯子。」她指着吧台上的三只锡杯,「现在中间这一只下面,藏着一颗能实现愿望的星星。接下来我会不断交换它们的位置,你猜星星在哪个杯子下。猜对了,星星归你。猜错了……您就付我一点“记忆”。」
哈哈,都什么跟什么,小孩子游戏。
拉斯马斯本该离开。但他刚结束一场八小时的手术,病人没能下手术台,血液与生命在手下流逝的空虚感此刻在指尖搏动。幻觉也好,恶作剧也罢,他需要一点别的东西来覆盖那段记忆。
「好。我玩。」拉斯马斯坐到女孩身边。
「那么,游戏开始咯。请看好。」
她没有像街头骗术那样快速移动杯子,反而极优雅地将它们扣着滑行,杯脚与木质台面缓缓摩擦。
「停。」 女孩双手离开杯子,乖巧地交叠在膝上。杯子静静立在那里,在吧台灯光下投出三个短短的影子,毫无分别。
拉斯马斯根本没注意看,随手指向中间的杯子。
「第一回就少取一些……」女孩脱掉皮鞋转向拉斯马斯,对他伸脚,「就取走您这次失败手术的记忆吧。」
「什么——」
女孩的粉袜脚掌踩上拉斯马斯的下体。
「你干什么——」拉斯马斯慌乱四下张望,寥寥两三个客人都专注于自己的酒杯,没有人在意这边发生了什么。女孩开始用脚隔着裤子揉搓着他的肉棒。
「你别胡闹了!」
女孩没有理睬,另一只脚也踩了上来,两只小脚灵活地在拉斯马斯裆部扭动。酥麻快感从裤子里蔓延开。
「唔呃呃……怎么会这么……舒服……」
没一会,他就在粉袜子的蹂躏下射出疲惫的精液。然而裤子并没被沾湿,果真如女孩所言,袜尖像是漩涡吸盘一样把精液连同他脑中的记忆片段尽数吞噬,只留下一腔记忆空洞。他忘了自己今晚在为谁动刀,忘了那具尸体的名字。今晚医疗事故的所有声音色彩细节都溶解进了女孩的脚底。
「您输了哦,拉斯马斯先生。不过,这下你该相信我的魔法了吧?」女孩收回双脚,「要继续吗?」
拉斯马斯还沉浸在射精与记忆抽取后的双重空虚中,茫然点头。直到女孩停止交换杯子,他才清醒过来,察觉不妙。
「我不玩了,我要走了!」
「不可以呢。」女孩脚一蹬椅子,飘落进斯马斯的怀里,轻轻揽住他的脖子,双脚直接探进他的裤腰带内,贴上肉棒,「中途离开游戏是犯规,犯规就要受罚。」
「你要干什么?!放开我!!」
「你看,你的小鸡鸡又硬起来了。它很喜欢我的脚呢,虽然只是小孩子的脚丫……但是我只要一按摩,它就会缠上我的脚。」女孩一边用双脚夹住拉斯马斯的肉棒上下撸动,一边坏笑,「来~让我听听,它到底在求什么……哦~原来你的小弟弟,想要再输一次呢~再让你输,再抽一次你的记忆,让他舒舒服服射精哦~」
「快停,快下来!不可以……」
「瞧~你的小弟弟在点头哦~看,它已经按耐不住了~」 女孩双脚加快了频率。
「这次是您去年平安夜,母亲给您织的新毛衣带来的温暖记忆。」女孩的手指轻点在他的太阳穴。
「呃啊啊啊啊啊啊——」
拉斯马斯第二波高潮来得更快,随着粉袜脚的蠕动,他再度败北。母爱与节日温馨融化在女孩的足底,而他对此一无所知。
「怎么样,还要再来么?」女孩松开拥抱。
拉斯马斯急切地往后挪动,大口喘气:「不要!我不想再玩了!」
「嘘,我没有在问您。您的小弟弟显然意犹未尽呢~」女孩调皮地说,「没关系~只要猜中一次,之前全部的失败都会补偿回来~」
只能陪她玩了吗?
女孩又交换了一遍三个锡杯位置。
这次拉斯马斯仔细盯着看着,轮到指认时,拉斯马斯选择左边那只锡杯:「我选左边这只!」
「看看是不是呢~」
女孩掀开左杯,是空的。
「我明明记得很清楚!」他说着就要伸手打开剩下的锡杯看个究竟。
「擅自触碰未选中的杯子也是犯规哦。双倍惩罚。」女孩又蹭到拉斯马斯身上,双脚再次探入裤裆,双手也攀上了他的两个乳头。「这次……索要的是您“面对血不晕眩的勇气”、“认出所有骨骼名称的知识”,嗯……“未来第一次主刀的成就感”也帮你预支了~」
「住手!那种记忆怎么能——」
「是呢,就是重要所以我才要把它偷走哦。」
「啊啊啊啊啊啊~~!」
当女孩的双脚覆上肉棒,乳头也遭到抓挠,快感与记忆绞在一起。失去这两样东西,身为外科医生的尊严、职业价值,拉斯马斯都会失去吧。他在恐惧与绝望中爆发,惨烈射精的同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真的开始离书本上的知识越来越远。
「你这个恶魔……!!」
「呵,您早该发现的。一个深夜酒馆里的红衣女童,不是恶魔还能是什么呢?但您还是决定来陪我玩了~」她晃了晃腿上的粉袜,其中传来精液吸收的咕噜声,「唯一的解释是,您是恋童癖,明知危险与不合理却屈服于欲望凑上来的恋童癖。而我袜子里都只是您这种劣等生物微不足道的记忆罢了~」
他的视线开始模糊。吧台对面的镜子里,他看见自己的眼睛渐渐失去光泽,肩膀微微垮塌。
「最后一轮,这次你可以选择离开,我不会拦你了,」女孩的声音从耳边传来,「如果猜对了,您之前输掉的一切记忆,我加倍偿还。」
拉斯马斯知道酒馆里有人,他有想过喊人求救,但是在小女孩脚下被欺辱榨精的事如果大声宣扬出来,不久坐实自己是个恋童癖了吗?那种事情一旦发生,他就没法作为正常人类生活下去了。只要不被其他人看到,说不定可以装作这一切都没发生,他至少还维持正常的助理医师生活。即使失去一些专业知识,日后重新学习也并非难事。
更何况……接连射精三次的痛苦之后,女孩的脚给他带来了奇妙的感受,他还想再体验一次。
拉斯马斯盯着女孩嘲弄的双眸。他的理性在尖叫,但内心深处传来一种自毁的冲动,一种想看看自己究竟能堕落到什么程度的病态好奇控制了他。
「……我继续。」
女孩微笑着伸出双手,再一次交换了那三个杯子的位置。
「我选中间。」
「哦呀?选这么快?最后一局了,不再考虑一下吗?」
「……。」
女孩轻轻抬起中央那只锡杯,下面只有一小块吧台木纹。
「彻底失败。」女孩趴进拉斯马斯怀里,双臂环抱住他的脖子,双脚夹住他的肉棒,「那么,把一切都给我吧,一切。您的知识、记忆、童年、爱情,除了关于我的记忆外,我都收下了。」
「等等……等等!你没说要……!」
「嗯?游戏之前我可是征得您同意了,取走什么记忆的选择权在我手里,您好像没什么资格阻止我呢~ 现在……让这双可爱的袜子成为您精液与灵魂的棺材吧~」女孩双脚发力,开始发狂研磨,十根脚趾紧紧夹住棒身,直接嵌进皮肉里。
「啊啊……」
「深~呼~吸~放~轻~松~把脑子清空~然后射出来啊~」
「啊……啊…啊……别……」
「很好~就是这样……来~给我的双脚,献上您全部的记忆吧~」
女孩用力一夹,拉斯马斯连续不断地射出精液,伴随着的是灵魂与记忆的大量流失。他就这样被女孩剥夺得一干二净。
圣诞女孩凭空消失,拉斯马斯重重倒在吧台上,昏睡过去。
酒馆外的街道上响起欢庆的圣诞歌,音乐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掩盖了刚才这出滑稽闹剧。
平安夜 PM 10:55
亨里克·索伦森刚从港口区一间私人俱乐部回来,公文包里装着一些绝不能让人看见的东西——项圈、束带、鞭子、手套。俱乐部主人称他为“虎鲸先生”,因为他在极度兴奋时的射精的力道与分量极其夸张,如同虎鲸换气时喷射的水柱,几乎能把人掀翻。俱乐部成员从不问他的全名或职业。在之前一小时里,他跪在波斯地毯的密室中,由一位戴黑面具的女子一边用平缓语调诵读《圣经·利未记》的段落一边不断在其背上抽打。
他需要这个。需要有人用不容置疑的力度按下他的肩膀,需要有人命令他“不准动”、“不准出声”,需要有人带给他疼痛。在银行里,他是发号施令的部门主管,在家庭,他是玛蒂尔德的模范丈夫。只有在俱乐部,在可以放下一切社会身份的地方,他才能暂时卸下一切伪装,赤裸裸地站在自己的欲望面前。
亨里克瞥见街灯下有个在积雪中快速走动的小小身影。是个男孩,大约十二三岁,穿海军蓝厚呢大衣,围着一条乳白色的羊绒围巾。那男孩脚步匆匆,脸上却刻意维持平静。这种神态亨里克在银行见过太多,都是在恐惧下试图维持体面的狼狈罢了。
「孩子,干什么去?今年街上没有聚会。」亨里克假装没看出他的慌张。
「先生……」男孩这才注意到旁边有个人,「您……您看见了吗?那东西。」他指身后上方。
亨里克眯眼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街灯铁柱顶端,蹲着一只渡鸦,体型巨大,身形隐没在黑暗里。在风雪天里看到只大渡鸦,确实有些反常。按理说它们早就迁徙了才对。
亨里克下意识把公文包换到远离男孩的一侧身体:「一只鸟?只是风雪天迷路的了吧。怎么了?」
「它一直跟着我,」男孩的声音压低下去,「它肯定不是鸟。它从我家窗户外,跟过了我三条街。飞起来没有声音,降落后也不叫唤……不像活的。我父亲……我父亲认识一些工坊的人,他们能做会动的机械鸟,说不定……」
结合男孩少爷般的穿着,亨里克恍然大悟:「所以你觉得那是你父母派来跟着你的,对吗?」
男孩猛抬头,尴尬地挠了挠脸腮:「是、是的,先生。」
「你应该回家,现在不适合在街上乱走。」亨里克说,语气里不自觉带出在银行里训导年轻职员的习惯性权威,「世界上没有能精密到这种程度,还能在风雪里追踪的机械鸟。」
雪花落在两人之间。亨里克沉默着,点燃一支烟。
男孩看他吞云吐雾,先一步打破沉默:「我的父母,他们不喜欢我“乱跑”。有时候觉得,我才是那个被上好发条的机械。」
「所以你就逃出来了?」亨里克呼出烟雾,「结果呢?你证明自己不是机械了吗?」
「没有……」男孩咬了下嘴唇。
「我看出来了,我也并不真的认为你只是个胡思乱想、离家出走的小孩。你隐瞒了不少东西。」亨里克缓缓开口,目光落在远处朦胧的暖黄色窗户上,那是他家的方向,「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觉得“得体”是世界上最沉重的盔甲。穿着它,你不能跑,不能喊,不能对想要的东西露出渴望,不能对厌恶的东西吐口水。后来我发现,成年后,东西也还是那套东西,只是换了名字,叫“责任”。」
男孩专注地听着。
「我也有必须藏起来的部分。一些绝不会被我的世界认可的渴望。每次有不得体的念头时,」他提起手中的公文包,轻轻晃了晃,「我就把它锁在包里,锁在只有特定夜晚特定地点才敢打开的房间里。我以为藏好了就没事。」
他抬头,看了眼那只静默的巨大渡鸦。
「可它跟着你,是不是?」亨里克转向男孩,「就像有些东西,无论你锁得多好,它都知道你在哪里。它不一定是机械,孩子。有时候,它就是你不敢承认的那部分自己,长出了眼睛和翅膀,在外面盯着你,等你崩溃。」
「那……怎么办?一直跑吗?」
「或者,」亨里克把烟头狠狠砸紧雪里,「转过身,面对它。告诉它你知道了。告诉它你受够了躲藏。」
他随即看向男孩:「你今晚偷跑出来,是想去找什么?真的只是想反抗父母的控制吗?嗯?你不妨坦率一点。」
男孩的脸颊红起来:「我……我看那些骑士小说,里面的英雄,总会遇到一段完全出乎意料的奇遇,没有安排,没有算计,像礼物一样。」他鼓起勇气,那双湛蓝的眸子里闪烁着羞怯与炽热,「我也……我也想遇到点什么,在不被人监视的地方,遇到一点真实的,没有被安排好的,哪怕是危险的“罗曼蒂克”。我想知道,我自己当主角的故事究竟会发生什么。」
「那就去。」亨里克说,「只要是你想做的,就去。至于这玩意儿…」他再次看向街灯上的渡鸦黑影。
亨里克突然做出了连自己都意外的举动。他猛地抡起公文包,用尽全力朝街灯顶端掷去。
「滚开!」
公文包并未击中渡鸦,它啪嗒一声笨重地落在远处积雪里。那只黑色生物受惊而起,几簇黑羽飘落,消失在茫茫雪花深处。
亨里克甩甩手,看着渡鸦消失的方向,又看看地上那个半埋入雪的公文包,好像那一掷,某些长久压着他的东西也被卸了下来。
男孩张大了嘴看着这个突然冒出野性的男人。
「先生,您的包……」
「没关系。」亨里克打断他,「里面装的不再是不体面的东西了。听着孩子,我向你保证,你自由了,至少今晚那只“机械鸟”不会再跟着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孩子。但要小心,注意安全。」
男孩站直了身体,郑重道:「谢谢您,先生。我会小心的。希望您也能随心做想做的事。」
「我会的……」亨里克轻声说,「但愿我会……」他的目光望向自家那扇暖黄色的窗户。这一次,他不想逃了。他打算与妻子玛蒂尔德坦白俱乐部的一切,展开一场困难而真实的对话。
「圣诞快乐,先生。」男孩朝他最后一鞠躬,走入飘雪的街道。
……
公文包的扣子开了,项圈已经从中露出大半。亨里克并没有立刻去收拾公文包。他在风雪中站了一会儿,享受秘密公开曝露于雪地之上的冰冷与轻松。然后才慢慢走过去,拎起来,重新赶往回家的路。
亨里克·索伦森刚从港口区一间私人俱乐部回来,公文包里装着一些绝不能让人看见的东西——项圈、束带、鞭子、手套。俱乐部主人称他为“虎鲸先生”,因为他在极度兴奋时的射精的力道与分量极其夸张,如同虎鲸换气时喷射的水柱,几乎能把人掀翻。俱乐部成员从不问他的全名或职业。在之前一小时里,他跪在波斯地毯的密室中,由一位戴黑面具的女子一边用平缓语调诵读《圣经·利未记》的段落一边不断在其背上抽打。
他需要这个。需要有人用不容置疑的力度按下他的肩膀,需要有人命令他“不准动”、“不准出声”,需要有人带给他疼痛。在银行里,他是发号施令的部门主管,在家庭,他是玛蒂尔德的模范丈夫。只有在俱乐部,在可以放下一切社会身份的地方,他才能暂时卸下一切伪装,赤裸裸地站在自己的欲望面前。
亨里克瞥见街灯下有个在积雪中快速走动的小小身影。是个男孩,大约十二三岁,穿海军蓝厚呢大衣,围着一条乳白色的羊绒围巾。那男孩脚步匆匆,脸上却刻意维持平静。这种神态亨里克在银行见过太多,都是在恐惧下试图维持体面的狼狈罢了。
「孩子,干什么去?今年街上没有聚会。」亨里克假装没看出他的慌张。
「先生……」男孩这才注意到旁边有个人,「您……您看见了吗?那东西。」他指身后上方。
亨里克眯眼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街灯铁柱顶端,蹲着一只渡鸦,体型巨大,身形隐没在黑暗里。在风雪天里看到只大渡鸦,确实有些反常。按理说它们早就迁徙了才对。
亨里克下意识把公文包换到远离男孩的一侧身体:「一只鸟?只是风雪天迷路的了吧。怎么了?」
「它一直跟着我,」男孩的声音压低下去,「它肯定不是鸟。它从我家窗户外,跟过了我三条街。飞起来没有声音,降落后也不叫唤……不像活的。我父亲……我父亲认识一些工坊的人,他们能做会动的机械鸟,说不定……」
结合男孩少爷般的穿着,亨里克恍然大悟:「所以你觉得那是你父母派来跟着你的,对吗?」
男孩猛抬头,尴尬地挠了挠脸腮:「是、是的,先生。」
「你应该回家,现在不适合在街上乱走。」亨里克说,语气里不自觉带出在银行里训导年轻职员的习惯性权威,「世界上没有能精密到这种程度,还能在风雪里追踪的机械鸟。」
雪花落在两人之间。亨里克沉默着,点燃一支烟。
男孩看他吞云吐雾,先一步打破沉默:「我的父母,他们不喜欢我“乱跑”。有时候觉得,我才是那个被上好发条的机械。」
「所以你就逃出来了?」亨里克呼出烟雾,「结果呢?你证明自己不是机械了吗?」
「没有……」男孩咬了下嘴唇。
「我看出来了,我也并不真的认为你只是个胡思乱想、离家出走的小孩。你隐瞒了不少东西。」亨里克缓缓开口,目光落在远处朦胧的暖黄色窗户上,那是他家的方向,「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觉得“得体”是世界上最沉重的盔甲。穿着它,你不能跑,不能喊,不能对想要的东西露出渴望,不能对厌恶的东西吐口水。后来我发现,成年后,东西也还是那套东西,只是换了名字,叫“责任”。」
男孩专注地听着。
「我也有必须藏起来的部分。一些绝不会被我的世界认可的渴望。每次有不得体的念头时,」他提起手中的公文包,轻轻晃了晃,「我就把它锁在包里,锁在只有特定夜晚特定地点才敢打开的房间里。我以为藏好了就没事。」
他抬头,看了眼那只静默的巨大渡鸦。
「可它跟着你,是不是?」亨里克转向男孩,「就像有些东西,无论你锁得多好,它都知道你在哪里。它不一定是机械,孩子。有时候,它就是你不敢承认的那部分自己,长出了眼睛和翅膀,在外面盯着你,等你崩溃。」
「那……怎么办?一直跑吗?」
「或者,」亨里克把烟头狠狠砸紧雪里,「转过身,面对它。告诉它你知道了。告诉它你受够了躲藏。」
他随即看向男孩:「你今晚偷跑出来,是想去找什么?真的只是想反抗父母的控制吗?嗯?你不妨坦率一点。」
男孩的脸颊红起来:「我……我看那些骑士小说,里面的英雄,总会遇到一段完全出乎意料的奇遇,没有安排,没有算计,像礼物一样。」他鼓起勇气,那双湛蓝的眸子里闪烁着羞怯与炽热,「我也……我也想遇到点什么,在不被人监视的地方,遇到一点真实的,没有被安排好的,哪怕是危险的“罗曼蒂克”。我想知道,我自己当主角的故事究竟会发生什么。」
「那就去。」亨里克说,「只要是你想做的,就去。至于这玩意儿…」他再次看向街灯上的渡鸦黑影。
亨里克突然做出了连自己都意外的举动。他猛地抡起公文包,用尽全力朝街灯顶端掷去。
「滚开!」
公文包并未击中渡鸦,它啪嗒一声笨重地落在远处积雪里。那只黑色生物受惊而起,几簇黑羽飘落,消失在茫茫雪花深处。
亨里克甩甩手,看着渡鸦消失的方向,又看看地上那个半埋入雪的公文包,好像那一掷,某些长久压着他的东西也被卸了下来。
男孩张大了嘴看着这个突然冒出野性的男人。
「先生,您的包……」
「没关系。」亨里克打断他,「里面装的不再是不体面的东西了。听着孩子,我向你保证,你自由了,至少今晚那只“机械鸟”不会再跟着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孩子。但要小心,注意安全。」
男孩站直了身体,郑重道:「谢谢您,先生。我会小心的。希望您也能随心做想做的事。」
「我会的……」亨里克轻声说,「但愿我会……」他的目光望向自家那扇暖黄色的窗户。这一次,他不想逃了。他打算与妻子玛蒂尔德坦白俱乐部的一切,展开一场困难而真实的对话。
「圣诞快乐,先生。」男孩朝他最后一鞠躬,走入飘雪的街道。
……
公文包的扣子开了,项圈已经从中露出大半。亨里克并没有立刻去收拾公文包。他在风雪中站了一会儿,享受秘密公开曝露于雪地之上的冰冷与轻松。然后才慢慢走过去,拎起来,重新赶往回家的路。
平安夜 PM11:03
阿卡塞尔·范·德·维尔登,十三岁,蓝眼睛,浅金色的头发点缀着雪花,海军蓝厚呢大衣的双排黄铜纽扣正一丝不苟扣好。他的家里有十七个房间和一只叫“老绅士”的圣伯纳犬。这个时间,他本该在享用完圣诞大餐后在温暖的卧室里熟睡。但他不想放弃体验真实圣诞节与“罗曼蒂克”的机会,特地等家人睡下后偷偷溜了出来。
莉瓦坐在垃圾桶旁,火红的大衣与周遭灰暗格格不入,正因如此,阿卡塞尔在街边看见莉瓦时,骑士小说里所有关于落难公主的章节都在他脑子里浮现。她看起来那么小,又有张那么淑女的脸……
「小姐!」他小跑过去,郑重地脱下手套,「你需要帮助吗?这样子待在街上会冻坏的。」
他迅速解下自己脖子上乳白色羊绒围巾,仔细地缠绕在莉瓦裸露的脖颈上。
「我在卖袜子,爸爸要我把所有袜子都卖掉,」莉瓦道,「可是……一直没人买。」
阿卡塞尔目光扫过两双袜子——灰色那双太普通,红白条纹的长袜又显然是双女孩子的款式。
或者……可以把那双长袜当圣诞礼物袜挂在床头?
想到此处,他掏出一张五十克朗递过去。
「给你,两双都买了。」他把钱放进莉瓦冰凉的手心,「灰的那双送你了,你快穿上回家吧,外面太冷。」
「谢谢您,」莉瓦微笑,「不过呀,除了钱以外,买下袜子还需要支付一些“快乐”。您愿意分享一点点您的“快乐”给我吗?一点点就好。」莉瓦说着,轻轻舔了一下嘴唇边缘。
「什……什么是“快乐”?」
「“快乐”嘛,它…」莉瓦拉住阿卡塞尔的手,「有点复杂,我来教你吧。我们去那边的小巷子里好吗?」
「好……好的。要多久?」
「不会很久的。」
莉瓦说着,把他引向小巷子。
阿卡塞尔·范·德·维尔登,十三岁,蓝眼睛,浅金色的头发点缀着雪花,海军蓝厚呢大衣的双排黄铜纽扣正一丝不苟扣好。他的家里有十七个房间和一只叫“老绅士”的圣伯纳犬。这个时间,他本该在享用完圣诞大餐后在温暖的卧室里熟睡。但他不想放弃体验真实圣诞节与“罗曼蒂克”的机会,特地等家人睡下后偷偷溜了出来。
莉瓦坐在垃圾桶旁,火红的大衣与周遭灰暗格格不入,正因如此,阿卡塞尔在街边看见莉瓦时,骑士小说里所有关于落难公主的章节都在他脑子里浮现。她看起来那么小,又有张那么淑女的脸……
「小姐!」他小跑过去,郑重地脱下手套,「你需要帮助吗?这样子待在街上会冻坏的。」
他迅速解下自己脖子上乳白色羊绒围巾,仔细地缠绕在莉瓦裸露的脖颈上。
「我在卖袜子,爸爸要我把所有袜子都卖掉,」莉瓦道,「可是……一直没人买。」
阿卡塞尔目光扫过两双袜子——灰色那双太普通,红白条纹的长袜又显然是双女孩子的款式。
或者……可以把那双长袜当圣诞礼物袜挂在床头?
想到此处,他掏出一张五十克朗递过去。
「给你,两双都买了。」他把钱放进莉瓦冰凉的手心,「灰的那双送你了,你快穿上回家吧,外面太冷。」
「谢谢您,」莉瓦微笑,「不过呀,除了钱以外,买下袜子还需要支付一些“快乐”。您愿意分享一点点您的“快乐”给我吗?一点点就好。」莉瓦说着,轻轻舔了一下嘴唇边缘。
「什……什么是“快乐”?」
「“快乐”嘛,它…」莉瓦拉住阿卡塞尔的手,「有点复杂,我来教你吧。我们去那边的小巷子里好吗?」
「好……好的。要多久?」
「不会很久的。」
莉瓦说着,把他引向小巷子。
平安夜 PM11:05
拉斯马斯怀念自己还能拿得起手术刀的岁月。从那年起,每个平安夜,拉斯马斯都会不由自主地走进鲱鱼酒馆。他的职位一年年下降,从助理医师到护士,再到被开除。
而他魂牵梦绕的那个圣诞女孩,再也没有出现过。
今天他也惯例在平安夜被酒保和常客们给轰了出来。酒馆大门在身后轰然关闭,他踉跄几步,光脚踩进积雪里。
酒馆招牌上那只木质鲱鱼在煤气灯下投出摇曳的黑影,飘荡在他茫然的脸前。酒馆里断续飘出跑调的圣诞颂歌。身体里那些被圣诞女孩挖走的空洞开始在寒风中发出呼啸。
回去吧。回去?回哪呢?
拉斯马斯漫无目的地游荡。
拉斯马斯怀念自己还能拿得起手术刀的岁月。从那年起,每个平安夜,拉斯马斯都会不由自主地走进鲱鱼酒馆。他的职位一年年下降,从助理医师到护士,再到被开除。
而他魂牵梦绕的那个圣诞女孩,再也没有出现过。
今天他也惯例在平安夜被酒保和常客们给轰了出来。酒馆大门在身后轰然关闭,他踉跄几步,光脚踩进积雪里。
酒馆招牌上那只木质鲱鱼在煤气灯下投出摇曳的黑影,飘荡在他茫然的脸前。酒馆里断续飘出跑调的圣诞颂歌。身体里那些被圣诞女孩挖走的空洞开始在寒风中发出呼啸。
回去吧。回去?回哪呢?
拉斯马斯漫无目的地游荡。
好…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