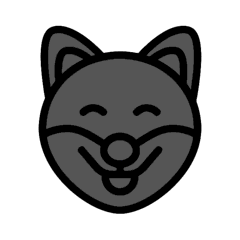浮生(NTR)
原创预览NTR绿奴情侣主
lianmo68发布于 ,编辑于 2026-02-04 09:53
浮生(NTR)
第一部已完结,7w多字
如需购买请加qq 3351449967
浮生 作者:liamo68
第1章【晨光】
第2章【宿怨】
第3章【滋养】
第4章【樱落】
第5章【禁果】
第6章【潮涌】
第7章【织梦】
第8章【溺爱】
第9章【流年】
第10章【尘埃】
第11章【困惑】
第12章【誓言】
第13章【妄念】
第14章【折戟】
第15章【决绝】
第16章【离愁】
第17章【乡音】
第18章【共鸣】
第19章【疏离】
第20章【春梦】
第21章【浮华】
第22章【夜叙】
第23章【两难】
第24章【葬心】
如需购买请加qq 3351449967
浮生 作者:liamo68
第1章【晨光】
第2章【宿怨】
第3章【滋养】
第4章【樱落】
第5章【禁果】
第6章【潮涌】
第7章【织梦】
第8章【溺爱】
第9章【流年】
第10章【尘埃】
第11章【困惑】
第12章【誓言】
第13章【妄念】
第14章【折戟】
第15章【决绝】
第16章【离愁】
第17章【乡音】
第18章【共鸣】
第19章【疏离】
第20章【春梦】
第21章【浮华】
第22章【夜叙】
第23章【两难】
第24章【葬心】
lianmo68发布于 ,编辑于 2026-01-23 21:54
Re: 浮生(NTR)
第1章【晨光】
十一月的晨光斜斜地洒在镇中操场的煤渣跑道上,空气清冽,夹杂着一丝干草与尘土的气息。看台上,学生们挤作一团,彩旗在微风中猎猎作响,广播里激昂的进行曲刚歇,紧接着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
“加油!加油!冲啊——!”
跑道中央,一道红色身影如离弦之箭,远远甩开身后众人,率先撞线。她双臂高举,马尾辫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额前的碎发已被汗水打湿,紧贴在光洁的额头上。
“第一名——周雨曦!”体育老师手持扩音器,声音洪亮地宣布。
我早已站在终点线旁,心口怦怦直跳。看到她冲过来的瞬间,我几乎要跳起来。她脚步放缓,喘着气朝我奔来,脸上挂着胜利的得意。
“累坏了吧?”我递上毛巾,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雀跃。
她一把扯过毛巾,胡乱擦了擦额头,斜瞥我一眼,嘴角微微上扬:“傻瓜,一百米短跑,能累到哪儿去?”
我嘿嘿一笑,没说话,只是伸手接过她擦完的毛巾,又轻轻替她擦脖子后面的汗珠。她的皮肤温热,带着运动后的微红,那股熟悉的、混合着青草与少女气息的味道让我耳根悄悄发烫。
这是镇上唯一的一所初中,平日里灰扑扑的,连教学楼外墙的白漆都斑驳得像被岁月啃过。可今天,因为这场运动会,整座学校仿佛活了过来。操场上彩旗招展,广播里不时插播着各班的加油稿。跑道一圈不到三百米,踩上去脚底还能听见煤渣碎裂的细响。看台是水泥砌的,斑驳掉漆,却坐满了人。
我们不过是初二的学生,可在彼此眼里,仿佛已是全世界。
周雨曦是我的女朋友——这个词说出来总让我有点脸红。不怪我早恋,我们确实是两情相悦。
初一刚开学,我们被分到同桌。她坐我右边,个子高,皮肤白,可成绩嘛……数学卷子上经常爬满红叉。我帮她补习数学,讲题时她会托着腮,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偶尔还会凑近,轻声问:“这一步怎么来的?”
那时我就觉得——她真可爱,笑起来像夏天咬开的第一口西瓜,清爽又甜。
没想到有一天,她竟在放学路上拽住我的书包带,直截了当地说:“喂,我喜欢你,做我男朋友吧?”
我愣在原地,舌头打结,脸烫得仿佛能滴出血来。可心里却像放了烟花——其实,我早就喜欢她了,只是始终没敢开口。最后竟然要一个女生主动表白,我既羞愧又感动。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拼了命地对她好。
后来她笑我:“你可是全年级第一诶,我怕再不抢先,你就被别人拐走了。”
或许她真的被“学霸”光环吸引过,但真正留住她的,是我们之间的互补。
在这所没几个人真正用心读书的小镇初中里,我的成绩是断档式第一。最离谱的那次期末考试,我比第二名整整高出一百分。可我的身子单薄得风一吹就晃,体育课跑八百米能喘成风箱。
她成绩在中游徘徊,体育却是全校的天花板。田径项目不说了,百米冲刺连很多男生都追不上。但她最厉害的,是一手出神入化的羽毛球——球拍一挥,白羽如电,落地无声,只剩对手愣在原地。
她身上仿佛装着永动机,整天不是在跑,就是在跳,活力四射。我常常暗自纳闷:她难道不累吗?哪来那么多用不完的力气?而我却不爱动弹,走路都慢悠悠的,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不像个少年。
她大大咧咧,说话嗓门大;我则畏畏缩缩,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都腿软,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有一次晚自习后,她把我拉到教学楼后面那棵老槐树下,路灯昏黄,照得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她居高临下,在我唇上轻轻一碰,快得像蜻蜓点水,却让我整晚都睡不着。
那是我的初吻。
回家路上,我一路傻笑,心里既惶恐又甜蜜。我想,要是我爸妈知道他们那个老实巴交、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儿子,竟然在学校里偷偷谈恋爱、还被亲了……怕是要连夜翻出生辰八字,确认我是不是他亲生的。
此刻,站在操场上,看着她被阳光镀上金边的侧脸,我觉得,哪怕全世界都惊讶,我也愿意牵着她的手,一直跑下去。
只是……我心里悄悄别扭的,是她比我高出不少。
初一刚开学时,她只比我略高一点点,我还能自我安慰:女生发育早,男生嘛,后劲足,迟早追上来。那时我甚至偷偷量过,站直了肩膀只差半指,心里还暗自得意——再长半年,我就能俯视她了。
可如今,到了初二,这借口再也没法自欺欺人。一个暑假过去,她像雨后春笋似的,窜了好几厘米。肩线稳稳我高出一截,连马尾辫垂下来都快扫到我肩膀。每次站在一起,我都下意识挺直腰背,可那点徒劳的挣扎,反而显得更狼狈。
如今是九十年代末,小镇还困在缓慢的时光里,家家户户都紧巴巴的。水泥路只修到镇中心,村口是坑洼的泥路,下雨就泥泞难行。就连一包简简单单的方便面,都被孩子们视作难得一见的“奢侈零食”。
我家境还好。爸妈早几年在沿海做服装批发生意,虽谈不上大富,但在村里已算体面。家里新盖了二层小楼,彩电、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村人背地里说,我们家是“两大富户”之一——当然,这“富”也只是相对而言,无非是顿顿有肉,生病敢去医院罢了。
她家在隔壁村,住的是瓦顶土墙的老屋。她还有个弟弟,才上小学。家里所有的指望都压在她身上——不是指望她考大学,而是指望她早点毕业,好出去打工贴补家用。她爸妈非常偏心,好吃的、新衣裳,全留给她弟弟。鸡腿夹进弟弟碗里,她碗里永远是青菜豆腐。她妈妈常在镇口缝纫摊接活,却从没见她穿过一件新衣。
她从不提这些,从不说家里催她辍学,只是某次我问起未来,她眼睛忽然亮起来:“我想考体育大学,学羽毛球专业。”语气充满向往,像在说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可我知道,她吃不饱饭。
我们学校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体育老师。女老师姓林,长得漂亮,说话利落,她家在镇上开了好多店,非常有钱。关键是,她是个羽毛球狂热分子。也许是她不想错过周雨曦这个好苗子,也许是她终于找到了一个能陪她对打的搭子,林老师悄悄送了她一副正规球拍。从那以后,林老师常带她去镇上唯一的体育馆练球,每周四次,风雨无阻。
训练量大,她消耗也大,饭量惊人。食堂的五毛钱一份的素菜汤配米饭,她常常吃两份都压不住饿。有次,我们一起走在回教室的路上,她忽然低头,手按在肚子上,脸微微红了。我听见了——那声低低的“咕噜”,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我没多想,当晚就把口袋里的十块块钱塞进她手心。她愣住,要推回来,我只说:“你拿着,我今天吃撑了。”
后来,这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零花钱从十块变成二十块,有时甚至把早餐钱全给她——“你吃,我不饿。”其实我饿,饿得胃里像有只手在抓。
有几次,我整整一天只啃几个冷馒头,硬邦邦的,咽下去像吞石头。可看到她中午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肉丝面,眼睛亮起来的样子,我心里那点委屈就烟消云散了。
青春期饿肚子是什么滋味?骨头缝里都泛着酸,夜里腿抽筋,早上爬起来眼前发黑。体育课跑圈时,我腿软得像踩棉花,可她却越跑越快,像风掠过煤渣跑道。
我和她的身高差距,就在这种“此消彼长”中越来越大。我俩不再是同桌,我的座位越来越往前,她的座位越来越往后。
可我不在乎。真的,一点也不。
她就像我悄悄养在心口的一株花,根扎在我最柔软的地方。我宁愿自己矮一点,瘦一点,也要让她吃饱、跑快、跳高,长得更挺拔些,能伸手够到那个叫“体育大学”的梦。
那是我的雨曦。我发誓过要对她好。
在她奔跑时扬起的发梢里,在她喘着气朝我笑的瞬间,在她接过我递来的毛巾时指尖无意的轻触里……我看见了比身高更重要的东西——那是光,是我在灰扑扑的少年时代里,唯一敢偷偷攥紧的光。
十一月的晨光斜斜地洒在镇中操场的煤渣跑道上,空气清冽,夹杂着一丝干草与尘土的气息。看台上,学生们挤作一团,彩旗在微风中猎猎作响,广播里激昂的进行曲刚歇,紧接着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
“加油!加油!冲啊——!”
跑道中央,一道红色身影如离弦之箭,远远甩开身后众人,率先撞线。她双臂高举,马尾辫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额前的碎发已被汗水打湿,紧贴在光洁的额头上。
“第一名——周雨曦!”体育老师手持扩音器,声音洪亮地宣布。
我早已站在终点线旁,心口怦怦直跳。看到她冲过来的瞬间,我几乎要跳起来。她脚步放缓,喘着气朝我奔来,脸上挂着胜利的得意。
“累坏了吧?”我递上毛巾,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雀跃。
她一把扯过毛巾,胡乱擦了擦额头,斜瞥我一眼,嘴角微微上扬:“傻瓜,一百米短跑,能累到哪儿去?”
我嘿嘿一笑,没说话,只是伸手接过她擦完的毛巾,又轻轻替她擦脖子后面的汗珠。她的皮肤温热,带着运动后的微红,那股熟悉的、混合着青草与少女气息的味道让我耳根悄悄发烫。
这是镇上唯一的一所初中,平日里灰扑扑的,连教学楼外墙的白漆都斑驳得像被岁月啃过。可今天,因为这场运动会,整座学校仿佛活了过来。操场上彩旗招展,广播里不时插播着各班的加油稿。跑道一圈不到三百米,踩上去脚底还能听见煤渣碎裂的细响。看台是水泥砌的,斑驳掉漆,却坐满了人。
我们不过是初二的学生,可在彼此眼里,仿佛已是全世界。
周雨曦是我的女朋友——这个词说出来总让我有点脸红。不怪我早恋,我们确实是两情相悦。
初一刚开学,我们被分到同桌。她坐我右边,个子高,皮肤白,可成绩嘛……数学卷子上经常爬满红叉。我帮她补习数学,讲题时她会托着腮,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偶尔还会凑近,轻声问:“这一步怎么来的?”
那时我就觉得——她真可爱,笑起来像夏天咬开的第一口西瓜,清爽又甜。
没想到有一天,她竟在放学路上拽住我的书包带,直截了当地说:“喂,我喜欢你,做我男朋友吧?”
我愣在原地,舌头打结,脸烫得仿佛能滴出血来。可心里却像放了烟花——其实,我早就喜欢她了,只是始终没敢开口。最后竟然要一个女生主动表白,我既羞愧又感动。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拼了命地对她好。
后来她笑我:“你可是全年级第一诶,我怕再不抢先,你就被别人拐走了。”
或许她真的被“学霸”光环吸引过,但真正留住她的,是我们之间的互补。
在这所没几个人真正用心读书的小镇初中里,我的成绩是断档式第一。最离谱的那次期末考试,我比第二名整整高出一百分。可我的身子单薄得风一吹就晃,体育课跑八百米能喘成风箱。
她成绩在中游徘徊,体育却是全校的天花板。田径项目不说了,百米冲刺连很多男生都追不上。但她最厉害的,是一手出神入化的羽毛球——球拍一挥,白羽如电,落地无声,只剩对手愣在原地。
她身上仿佛装着永动机,整天不是在跑,就是在跳,活力四射。我常常暗自纳闷:她难道不累吗?哪来那么多用不完的力气?而我却不爱动弹,走路都慢悠悠的,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不像个少年。
她大大咧咧,说话嗓门大;我则畏畏缩缩,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都腿软,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有一次晚自习后,她把我拉到教学楼后面那棵老槐树下,路灯昏黄,照得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她居高临下,在我唇上轻轻一碰,快得像蜻蜓点水,却让我整晚都睡不着。
那是我的初吻。
回家路上,我一路傻笑,心里既惶恐又甜蜜。我想,要是我爸妈知道他们那个老实巴交、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儿子,竟然在学校里偷偷谈恋爱、还被亲了……怕是要连夜翻出生辰八字,确认我是不是他亲生的。
此刻,站在操场上,看着她被阳光镀上金边的侧脸,我觉得,哪怕全世界都惊讶,我也愿意牵着她的手,一直跑下去。
只是……我心里悄悄别扭的,是她比我高出不少。
初一刚开学时,她只比我略高一点点,我还能自我安慰:女生发育早,男生嘛,后劲足,迟早追上来。那时我甚至偷偷量过,站直了肩膀只差半指,心里还暗自得意——再长半年,我就能俯视她了。
可如今,到了初二,这借口再也没法自欺欺人。一个暑假过去,她像雨后春笋似的,窜了好几厘米。肩线稳稳我高出一截,连马尾辫垂下来都快扫到我肩膀。每次站在一起,我都下意识挺直腰背,可那点徒劳的挣扎,反而显得更狼狈。
如今是九十年代末,小镇还困在缓慢的时光里,家家户户都紧巴巴的。水泥路只修到镇中心,村口是坑洼的泥路,下雨就泥泞难行。就连一包简简单单的方便面,都被孩子们视作难得一见的“奢侈零食”。
我家境还好。爸妈早几年在沿海做服装批发生意,虽谈不上大富,但在村里已算体面。家里新盖了二层小楼,彩电、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村人背地里说,我们家是“两大富户”之一——当然,这“富”也只是相对而言,无非是顿顿有肉,生病敢去医院罢了。
她家在隔壁村,住的是瓦顶土墙的老屋。她还有个弟弟,才上小学。家里所有的指望都压在她身上——不是指望她考大学,而是指望她早点毕业,好出去打工贴补家用。她爸妈非常偏心,好吃的、新衣裳,全留给她弟弟。鸡腿夹进弟弟碗里,她碗里永远是青菜豆腐。她妈妈常在镇口缝纫摊接活,却从没见她穿过一件新衣。
她从不提这些,从不说家里催她辍学,只是某次我问起未来,她眼睛忽然亮起来:“我想考体育大学,学羽毛球专业。”语气充满向往,像在说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可我知道,她吃不饱饭。
我们学校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体育老师。女老师姓林,长得漂亮,说话利落,她家在镇上开了好多店,非常有钱。关键是,她是个羽毛球狂热分子。也许是她不想错过周雨曦这个好苗子,也许是她终于找到了一个能陪她对打的搭子,林老师悄悄送了她一副正规球拍。从那以后,林老师常带她去镇上唯一的体育馆练球,每周四次,风雨无阻。
训练量大,她消耗也大,饭量惊人。食堂的五毛钱一份的素菜汤配米饭,她常常吃两份都压不住饿。有次,我们一起走在回教室的路上,她忽然低头,手按在肚子上,脸微微红了。我听见了——那声低低的“咕噜”,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我没多想,当晚就把口袋里的十块块钱塞进她手心。她愣住,要推回来,我只说:“你拿着,我今天吃撑了。”
后来,这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零花钱从十块变成二十块,有时甚至把早餐钱全给她——“你吃,我不饿。”其实我饿,饿得胃里像有只手在抓。
有几次,我整整一天只啃几个冷馒头,硬邦邦的,咽下去像吞石头。可看到她中午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肉丝面,眼睛亮起来的样子,我心里那点委屈就烟消云散了。
青春期饿肚子是什么滋味?骨头缝里都泛着酸,夜里腿抽筋,早上爬起来眼前发黑。体育课跑圈时,我腿软得像踩棉花,可她却越跑越快,像风掠过煤渣跑道。
我和她的身高差距,就在这种“此消彼长”中越来越大。我俩不再是同桌,我的座位越来越往前,她的座位越来越往后。
可我不在乎。真的,一点也不。
她就像我悄悄养在心口的一株花,根扎在我最柔软的地方。我宁愿自己矮一点,瘦一点,也要让她吃饱、跑快、跳高,长得更挺拔些,能伸手够到那个叫“体育大学”的梦。
那是我的雨曦。我发誓过要对她好。
在她奔跑时扬起的发梢里,在她喘着气朝我笑的瞬间,在她接过我递来的毛巾时指尖无意的轻触里……我看见了比身高更重要的东西——那是光,是我在灰扑扑的少年时代里,唯一敢偷偷攥紧的光。
lianmo68发布于 2026-02-04 09:38
Re: 浮生(NTR)
第2章【宿怨】
“还说不累,汗越擦越多。”我一边替她擦汗,一边低声嘟囔,毛巾擦过她额角,又洇湿了一片。
她侧过头,故意凑近一步,带着几分狡黠:“是么?那味道是不是很大啊?”
话音未落,她笑嘻嘻地抬起胳膊,肘关节一弯,把汗津津的腋下朝我鼻尖怼过来。
我耳根一烫,赶紧伸手把她推开:“哎呀——别闹!臭死了!”
她却笑得更欢了,肩膀一耸一耸的:“才不臭呢!这可是冠军的味道!别人想闻还闻不到呢!”
她比我高出半头,做这种动作轻而易举,甚至带着点居高临下的得意。而且,她就爱这样——坐在我旁边时,总喜欢突然俯身、伸手、或者用各种出其不意的方式逗我。她似乎从这种小小的“欺负”里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有次更过分,她跑完三千米,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却不知从哪儿翻出一双捂了整整一场赛事的袜子,趁我不备,猛地捂在我鼻子上。那股浓烈的汗酸味直冲脑门,我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快出来了。
“周雨曦!你疯啦!” 我气急败坏地吼她。
她却“咯咯”笑着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朝我吐舌头,银铃般的笑声洒了一地。我拔腿去追,可腿脚发软,刚跑几步就气喘如牛,眼睁睁看着她越跑越远,最后站在操场另一头朝我挥手。我站在原地,又气又无奈,心里却悄悄泛起一丝甜。
她似乎很喜欢这类游戏——把汗味、臭袜子、喘息声,变成捉弄我的武器。起初我真觉得难为情,甚至有些排斥。可不知从哪天起,我竟开始贪恋这种气息——那种混合着体温、汗水和一点点盐分的味道,让我心头莫名安稳。可我不敢表现出来,更不敢多闻,怕她觉得我奇怪,怕她笑我“有病”。
接下来的日子,周雨曦简直像踩着风火轮——披荆斩棘,每一个项目都稳稳第一,出尽了风头。老师点名表扬,连校长在闭幕式上都特意提到她的名字。而我,则始终站在场边,手里攥着水壶和毛巾,目光追着她跑、跳、投、冲,一声声“加油”喊得嗓子都哑了。
我们俩就是这样,一文一武——我稳坐文化课第一,她横扫体育赛场。
持续三天的运动会就这样结束了。
夕阳把煤渣跑道染成橘红色,彩旗卷了边,看台上的人影散尽,连广播里的激昂旋律也沉寂下来。周雨曦拿了七个项目的第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跳高、跳远、铅球、四乘一百接力。奖状叠在她手里,像一沓轻飘飘的纸,可我知道,这都不是她真正想要的。
我们学校连一块像样的羽毛球场地都没有。水泥地裂缝里长着杂草,球网?从未见过。运动会项目表上,压根没有“羽毛球”三个字。她最引以为傲的那项本事,在这里,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
我走过去,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肘。她回过神,抬眼看向我,嘴角牵起一丝笑,可那笑意没到眼底。
“毕业后就不能跟林老师蹭球了,不知道高中有没有场地。”
“有的,”我脱口而出,“露天的,水泥地,但有正经球网。”
她眼睛倏地亮了一下:“真的?你去过?”
“当然啊。”我点头,“我跟我爸去县城买过球鞋,顺道转了转。”
她忽然笑起来,带着点不好意思的兴奋:“康康,啥时候你带我去逛逛吧?我只去过一回县城,那天本来想去看看学校的,结果我妈急着赶顺风车回村,我连街都没走完就被人拽上车了。”
“好啊。”我答应得毫不犹豫,心里却像被什么轻轻揪了一下。
我心想:这小姑娘真的太让人心疼了。这么大了,连县城都只去过一回。而我呢?去年冬天,爸妈还带我去黄山旅游了,坐了火车,住了宾馆,还在迎客松下拍了张全家福。
“回家了。”她的声音几乎融进了暮色里。
“嗯。”我应了一声,没多说。
她转身走了,背影被夕阳拉得又细又长。我站在原地,目送她走远,直到她的身影拐过校门,消失在那条通往隔壁村的土路上。
等她的身影彻底看不见了,我才从口袋里掏出那条为她擦过汗的毛巾,凑到鼻尖,深深吸了一口。
味道好极了。
————————————
回到家时,天已擦黑。灶间飘出青菜炖豆腐的香气,混着柴火烟味,本该是安稳的晚饭时分。可一进屋,我就愣住了——我爸坐在堂屋的竹椅上,额角缠着一圈白纱布,边缘渗着淡黄的药水渍。
“爸,这是怎么了?”我放下书包。
我妈从灶台边转过身,手里还攥着锅铲,叹了口气:“跟隔壁打起来了。”
“隔壁”——就是村里人口中“两大富户”里的另一家,余家。
他们家最近在造新楼房,红砖一层叠一层,水泥还没干透,就急着把院子往外扩,硬是把原本通向小河的路全占了。那路,是我妈每天洗衣的必经之道。如今,得绕过他家屋后那片荒了多年的荆棘丛,踩着烂泥走,多出整整十分钟,雨天更难行。
我爸是个讲理的人。他去了三次,第一次提着一包烟,客客气气;第二次语气更缓;第三次只说:“路窄点也行,留个脚宽就行。”可余家只冷冷一笑,站在新砌的砖墙后,抱着胳膊:“地是我家祖产,我想怎么修,轮不到你吴家指手画脚。”
村里调解员上门,他们连院门都没让进,只从门缝里扔出一句:“有本事,去告啊。”
“他们家就是这么不讲理,”我妈转过身,锅铲在灶沿上轻轻磕了一下,发出“当”的一声,“祖上就是——横的。”她咬牙切齿,可眼里更多的是无奈。
我们村,座落在江南腹地,小河穿村而过,白墙黑瓦,本该是温软水乡。可没人记得,百年前太平天国战火燎原,清军屠村,把村里杀得十室九空。后来迁来的,大多是江北逃荒的移民,连本地话都慢慢失传了。如今全村,只剩我们吴家和余家是土著。
可偏偏,这两家土著,从民国斗到现在,仇比河深。
早年听爷爷讲,民国时,两家老人前后脚过世。我家请了位有名的风水先生,看了块“聚气藏风”的宝地。说是埋下去,子孙兴旺,家业绵长。结果那风水图刚画完,余家连夜带人扛锄头去,把坟立在了正穴上。我家祖上气得吐血,从此立下铁律:吴余家,不通婚、不共席、不往来。
到了文革余家带头批斗我们家,说我太爷爷是“地主残余”,一把火把我家藏了几百年的族谱烧成了灰,连祖宗牌位都砸了。更狠的是,一个爷爷辈的长辈,被挂黑牌游街,三天后死在牛棚里,脚踝上还拴着铁链。
到了我爸这一辈,两家人都去沿海搞服装批发。同行如冤家,为了抢同一批单子,两家人在异乡的地头上也没少红过脸。
如今回了村,表面相安无事,背地里却处处较劲——像两股暗流,在平静的水面下撞得火星四溅。
他们家盖楼,故意把屋檐挑得比我家高;我家买了彩电,他们第二天就搬回一台双开门冰箱。
这次,终于撕破了脸,动了手。
我爸向来不愿掺和这些。他常说:“村里这些鸡毛蒜皮,争来争去,没意思。读书,才是真出路。”
到了我们这一代,因为计划生育,两家都只剩一个儿子——单传。
我,吴康;他们家,余昊。
我爸把所有希望都押在我身上,吴家唯一的独苗。他从不让我干农活,连扫地都少让我干,只说:“你只管读书。”我也争气,从小到大,成绩单上永远是第一名。
而余昊,他跟我同岁,小学就在隔壁班。他成绩平平,却生得高大结实,皮肤黝黑,浑身散发着使不完的蛮力。他体育天赋极高,尤其是打篮球时,三分线外拔地而起,手腕一抖,球“唰”地空心入网,惹得看台上的女生尖叫连连。
升入初中后,他没留在镇上。他爸托了关系,把他送到县城,寄住在那边定居的阿姨家,说是那边的体育训练条件更好。其实我爸妈也动过送我去县里、甚至市里读书的念头,可苦于城里没亲戚照应,终究只能作罢。
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但两家院墙挨着院墙,抬头不见低头见。每次在村道上撞上,我们谁也不看谁,仿佛对方只是团透明的空气。可我总能感觉得到——他掠过我时的眼神里,始终带着点说不出的……敌意。
“还说不累,汗越擦越多。”我一边替她擦汗,一边低声嘟囔,毛巾擦过她额角,又洇湿了一片。
她侧过头,故意凑近一步,带着几分狡黠:“是么?那味道是不是很大啊?”
话音未落,她笑嘻嘻地抬起胳膊,肘关节一弯,把汗津津的腋下朝我鼻尖怼过来。
我耳根一烫,赶紧伸手把她推开:“哎呀——别闹!臭死了!”
她却笑得更欢了,肩膀一耸一耸的:“才不臭呢!这可是冠军的味道!别人想闻还闻不到呢!”
她比我高出半头,做这种动作轻而易举,甚至带着点居高临下的得意。而且,她就爱这样——坐在我旁边时,总喜欢突然俯身、伸手、或者用各种出其不意的方式逗我。她似乎从这种小小的“欺负”里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有次更过分,她跑完三千米,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却不知从哪儿翻出一双捂了整整一场赛事的袜子,趁我不备,猛地捂在我鼻子上。那股浓烈的汗酸味直冲脑门,我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快出来了。
“周雨曦!你疯啦!” 我气急败坏地吼她。
她却“咯咯”笑着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朝我吐舌头,银铃般的笑声洒了一地。我拔腿去追,可腿脚发软,刚跑几步就气喘如牛,眼睁睁看着她越跑越远,最后站在操场另一头朝我挥手。我站在原地,又气又无奈,心里却悄悄泛起一丝甜。
她似乎很喜欢这类游戏——把汗味、臭袜子、喘息声,变成捉弄我的武器。起初我真觉得难为情,甚至有些排斥。可不知从哪天起,我竟开始贪恋这种气息——那种混合着体温、汗水和一点点盐分的味道,让我心头莫名安稳。可我不敢表现出来,更不敢多闻,怕她觉得我奇怪,怕她笑我“有病”。
接下来的日子,周雨曦简直像踩着风火轮——披荆斩棘,每一个项目都稳稳第一,出尽了风头。老师点名表扬,连校长在闭幕式上都特意提到她的名字。而我,则始终站在场边,手里攥着水壶和毛巾,目光追着她跑、跳、投、冲,一声声“加油”喊得嗓子都哑了。
我们俩就是这样,一文一武——我稳坐文化课第一,她横扫体育赛场。
持续三天的运动会就这样结束了。
夕阳把煤渣跑道染成橘红色,彩旗卷了边,看台上的人影散尽,连广播里的激昂旋律也沉寂下来。周雨曦拿了七个项目的第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跳高、跳远、铅球、四乘一百接力。奖状叠在她手里,像一沓轻飘飘的纸,可我知道,这都不是她真正想要的。
我们学校连一块像样的羽毛球场地都没有。水泥地裂缝里长着杂草,球网?从未见过。运动会项目表上,压根没有“羽毛球”三个字。她最引以为傲的那项本事,在这里,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
我走过去,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肘。她回过神,抬眼看向我,嘴角牵起一丝笑,可那笑意没到眼底。
“毕业后就不能跟林老师蹭球了,不知道高中有没有场地。”
“有的,”我脱口而出,“露天的,水泥地,但有正经球网。”
她眼睛倏地亮了一下:“真的?你去过?”
“当然啊。”我点头,“我跟我爸去县城买过球鞋,顺道转了转。”
她忽然笑起来,带着点不好意思的兴奋:“康康,啥时候你带我去逛逛吧?我只去过一回县城,那天本来想去看看学校的,结果我妈急着赶顺风车回村,我连街都没走完就被人拽上车了。”
“好啊。”我答应得毫不犹豫,心里却像被什么轻轻揪了一下。
我心想:这小姑娘真的太让人心疼了。这么大了,连县城都只去过一回。而我呢?去年冬天,爸妈还带我去黄山旅游了,坐了火车,住了宾馆,还在迎客松下拍了张全家福。
“回家了。”她的声音几乎融进了暮色里。
“嗯。”我应了一声,没多说。
她转身走了,背影被夕阳拉得又细又长。我站在原地,目送她走远,直到她的身影拐过校门,消失在那条通往隔壁村的土路上。
等她的身影彻底看不见了,我才从口袋里掏出那条为她擦过汗的毛巾,凑到鼻尖,深深吸了一口。
味道好极了。
————————————
回到家时,天已擦黑。灶间飘出青菜炖豆腐的香气,混着柴火烟味,本该是安稳的晚饭时分。可一进屋,我就愣住了——我爸坐在堂屋的竹椅上,额角缠着一圈白纱布,边缘渗着淡黄的药水渍。
“爸,这是怎么了?”我放下书包。
我妈从灶台边转过身,手里还攥着锅铲,叹了口气:“跟隔壁打起来了。”
“隔壁”——就是村里人口中“两大富户”里的另一家,余家。
他们家最近在造新楼房,红砖一层叠一层,水泥还没干透,就急着把院子往外扩,硬是把原本通向小河的路全占了。那路,是我妈每天洗衣的必经之道。如今,得绕过他家屋后那片荒了多年的荆棘丛,踩着烂泥走,多出整整十分钟,雨天更难行。
我爸是个讲理的人。他去了三次,第一次提着一包烟,客客气气;第二次语气更缓;第三次只说:“路窄点也行,留个脚宽就行。”可余家只冷冷一笑,站在新砌的砖墙后,抱着胳膊:“地是我家祖产,我想怎么修,轮不到你吴家指手画脚。”
村里调解员上门,他们连院门都没让进,只从门缝里扔出一句:“有本事,去告啊。”
“他们家就是这么不讲理,”我妈转过身,锅铲在灶沿上轻轻磕了一下,发出“当”的一声,“祖上就是——横的。”她咬牙切齿,可眼里更多的是无奈。
我们村,座落在江南腹地,小河穿村而过,白墙黑瓦,本该是温软水乡。可没人记得,百年前太平天国战火燎原,清军屠村,把村里杀得十室九空。后来迁来的,大多是江北逃荒的移民,连本地话都慢慢失传了。如今全村,只剩我们吴家和余家是土著。
可偏偏,这两家土著,从民国斗到现在,仇比河深。
早年听爷爷讲,民国时,两家老人前后脚过世。我家请了位有名的风水先生,看了块“聚气藏风”的宝地。说是埋下去,子孙兴旺,家业绵长。结果那风水图刚画完,余家连夜带人扛锄头去,把坟立在了正穴上。我家祖上气得吐血,从此立下铁律:吴余家,不通婚、不共席、不往来。
到了文革余家带头批斗我们家,说我太爷爷是“地主残余”,一把火把我家藏了几百年的族谱烧成了灰,连祖宗牌位都砸了。更狠的是,一个爷爷辈的长辈,被挂黑牌游街,三天后死在牛棚里,脚踝上还拴着铁链。
到了我爸这一辈,两家人都去沿海搞服装批发。同行如冤家,为了抢同一批单子,两家人在异乡的地头上也没少红过脸。
如今回了村,表面相安无事,背地里却处处较劲——像两股暗流,在平静的水面下撞得火星四溅。
他们家盖楼,故意把屋檐挑得比我家高;我家买了彩电,他们第二天就搬回一台双开门冰箱。
这次,终于撕破了脸,动了手。
我爸向来不愿掺和这些。他常说:“村里这些鸡毛蒜皮,争来争去,没意思。读书,才是真出路。”
到了我们这一代,因为计划生育,两家都只剩一个儿子——单传。
我,吴康;他们家,余昊。
我爸把所有希望都押在我身上,吴家唯一的独苗。他从不让我干农活,连扫地都少让我干,只说:“你只管读书。”我也争气,从小到大,成绩单上永远是第一名。
而余昊,他跟我同岁,小学就在隔壁班。他成绩平平,却生得高大结实,皮肤黝黑,浑身散发着使不完的蛮力。他体育天赋极高,尤其是打篮球时,三分线外拔地而起,手腕一抖,球“唰”地空心入网,惹得看台上的女生尖叫连连。
升入初中后,他没留在镇上。他爸托了关系,把他送到县城,寄住在那边定居的阿姨家,说是那边的体育训练条件更好。其实我爸妈也动过送我去县里、甚至市里读书的念头,可苦于城里没亲戚照应,终究只能作罢。
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但两家院墙挨着院墙,抬头不见低头见。每次在村道上撞上,我们谁也不看谁,仿佛对方只是团透明的空气。可我总能感觉得到——他掠过我时的眼神里,始终带着点说不出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