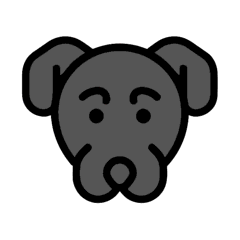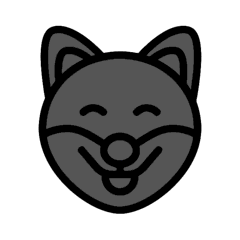【约稿】士(2026-01-26更新)
连载中原创现实情侣主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5-12-19 18:09
Re: Re: 【约稿】士(12.02更新)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5-12-19 18:11
Re: Re: 【约稿】士(12.02更新)
chromaso发布于 2026-01-11 17:02
Re: Re: 【约稿】士(11.08更新)
humulation:↑“那我接下来每抽你一下,你就说一句‘打得好’。”他命令道。还是觉得这一段很色啊!
我惊慌地看向她,她抱着胳膊,坐在床边,裹着腿套的小腿交叠在一起,制服鞋的鞋尖在地板上轻轻点着,没有说话。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6-01-11 21:22
Re: Re: Re: 【约稿】士(11.08更新)
chromaso:↑马索克觉得很淦()humulation:↑“那我接下来每抽你一下,你就说一句‘打得好’。”他命令道。还是觉得这一段很色啊!
我惊慌地看向她,她抱着胳膊,坐在床边,裹着腿套的小腿交叠在一起,制服鞋的鞋尖在地板上轻轻点着,没有说话。我也希望我主人能去找个男朋友来认真取代我啊,待我主人的男朋友拿衣架打我的时候,我会超大声地说「打得好」的!
coukou111别字小鬼发布于 2026-01-11 21:40
Re: 【约稿】士(12.02更新)
所以这篇还没有更新吗ww这都一个月啦!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6-01-12 18:47
Re: Re: 【约稿】士(12.02更新)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6-01-13 12:37
Re: Re: 【约稿】士(12.02更新)
humulation:↑这样吗,那就加油吧(睡瞌睡:↑慢工出细活嘛,不用操之过急(ˊᗜˋ*)我倒是不急啦,但是我对单主的责任心时时催我()
coukou111别字小鬼发布于 2026-01-13 13:31
Re: Re: Re: 【约稿】士(12.02更新)
humulation:↑真好啊……想当人仿老师的单主然后用小皮鞭狠狠地催更……睡瞌睡:↑慢工出细活嘛,不用操之过急(ˊᗜˋ*)我倒是不急啦,但是我对单主的责任心时时催我()
chromaso发布于 2026-01-13 13:37
Re: Re: Re: Re: 【约稿】士(12.02更新)
coukou111别字小鬼发布于 ,编辑于 2026-01-13 13:39
Re: Re: Re: Re: Re: 【约稿】士(12.02更新)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编辑于 2026-01-13 16:26
Re: Re: Re: Re: Re: Re: 【约稿】士(12.02更新)
coukou111别字小鬼发布于 2026-01-13 16:40
Re: Re: Re: Re: Re: Re: Re: 【约稿】士(12.02更新)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6-01-26 21:56
Re: 【约稿】士(2026-01-26更新)
# 15
时间是个比瓜田里的猹还要狡猾的小偷。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呢?是他不断表示想要她学习化妆的时候?是他在她面试前,非拉着她去买一双不舒服的高跟鞋的时候?是在他擅自买来符合男性审美的衣服,要她穿给她看的时候?还是每次她对未来有所规划,都被他以大创国奖得主的身份所劝退的时候?
我思来想去,想不明白。我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界限,一个足够大的事件,来解释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底是为什么,让事情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我察觉到的时候,一场没有铁幕演说的冷战早已在二人之间铺展开了,像夏夜森林中的磷火一样,安静地、冷酷地、幽灵似的燃烧着。
见面时,他们会下意识地绷紧身体,而这种紧绷很快就会发展成谈话中的对抗性态度,进而演变成敌意。但他们几乎不会争吵,最终结果基本上是以平静的散伙结束。可那并非真的平静,而是类似暴雨前夕,厚重的铅色的云凝在天上,让人的头发和汗毛都被头顶悬着的巨量电荷吸得竖立起来时,人所感受到的,庞大而无形的压力。
有什么东西在膨胀。就好像一个封闭的盒子里,装着两个气球,当气球膨胀起来的时候,盒子里的气压自然而然地就升高起来,压得人胸闷得喘不上气。
我当然能理解她为什么讨厌他的那些建议。他说的那些条条框框,在她看来不仅不符合女权主义的观念,过度迎合男权社会的规则和审美,而且存在着某种“改造”的意思:“我的能力在你之上,所以你要把我的建议奉为圭臬,削减自己的自由,按照我定下的金科玉律来改造自己。”她多半是这样解读的。
在我看来,他只是关心则乱,脑子里想说的建议太多了,再加上她的对抗性态度(人在受到反对时会愤怒,这是很正常的),说话的方式不自觉地变得直接了,说了不少直男发言,仅此而已。这算不得是什么错误,因为客观来看,他所说的东西确实基本都是对的,只是单纯的不符合她所崇尚的观念而已。
“他做过大创,拿过国奖,在路演和面试方面确实经验多些。虽然他说的那些大多都是学术圈的糟粕,是不良风气,但是这也确实是我国学术界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现状。”我如此劝慰她。
“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该放弃改变的努力。”她固执地说。
“这只是一厢情愿,力量弱小却还想着改变他人,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竹篮打水。”他立即反驳道。
“或许我们改天再商量这件事?”我打圆场。
于是一次次会面就这样在高度相似的沉默中解散。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明白我。”他愤愤地说,“我见过比赛圈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真的不是凭一个本科生就能改变的。”
“她多半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理解她吧。”我走在他并肩的位置,“她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情,很难对你说的那些产生共鸣。等她读研了,切身经历几次被抢一作二作,或者被导师要求把辛苦做完大半的项目让给师兄师弟的烂事,自然就会明白了。”
“到那时候就晚了,现在不赶紧努力的话,恐怕没法保 985 的研了。等到去了差学校再后知后觉地悔恨,那有什么用啊。”他说。
“倒也是。”我点点头。虽然我日子过得很佛系,但他们两个无疑是要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的。
“事到如今,我们两个必须联合起来了。”他说。
“怎么?”我问。
“我刚刚想了个计划,让她实际感受一次社会的黑暗,或许她就能正视现实了。”
“那很好啊,我扮演什么角色?”我走上前。
他停下脚步:“我要先声明,即使你参与进来,我也不会用平等的姿态和你共处,我依然会以男主人的身份命令你。”
“行。”我说。
他于是向我说了那个计划。
大胆,僭越,令人生畏。
# 16
简单来说,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她沉浸在一种“全能幻想”之中。她在想象中认为世界会按照她的命令而做出符合她心意的改变,但这只是她在全能自恋的视角下,对世界产生的扭曲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他打算安排一个适合辩论的场景,在模拟的情景中,用事实把她驳倒,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用真实的世界把她从全能自恋的镣铐中解救出来。
“所以我们搭建一个模拟的面试场景,让她体验一下刻薄的面试流程,感受一下科研圈子里的严肃压力,她应该就能认清现实了。”他站在讲台上,自信地说。
我有点犹豫,心里总觉得这有点过分了。但是面对着兴致勃勃的他,我也没法说出丧气的话来,只能嗯嗯啊啊地附和,不断点头,摆出完全听从他的调遣的样子。说到底,这是他们情侣之间的事情,轮不到我一个家臣来插手,我只要保持当个好用的工具就行了。
一周的时间里,我和他商量了具体的布置方案和简单的剧本,主体部分都是他提出的,我只增加一些边角的点缀。然后,按照计划,我去文印店做了一些桌牌之类的小道具,用来增加场景的真实感,他则去申请一间空教室作为场地。与此同时,由他去找她,半哄半骗地要她答应去参加一个“含金量很高的面试”。她不情不愿地同意了。
“今天可能会很难受,抱歉。”假面试的当天,我悄悄给她发消息。
她没有回复。
下午,我们在提前约好的教室等她。我坐在教室中后部,坐得很直,大脑像是收不到信号的电视屏幕,塞满了密密麻麻的噪点,喧闹成一片噪声的海洋,里面却没有任何内容。我的眼珠四处转动,企图发现哪怕一只在地上爬动的蚂蚁,能让我得以把无处安放的注意力寄托在它身上,可终究是徒劳无功,教室里什么也没有,我只能任由心脏在胸腔里从内而外地,像液压机一样地挤压我,把我挤扁成一个实心的垃圾块,方方正正地墩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他坐在教室第三排的位置,好整以暇地整理着西装,虽然只是在校门口商业街里的成衣店里买的工厂货,但他有着西服所最重要的配件——自信,在我看来,这便是一个足够耀眼的人了。
门外有人敲门。
“进!”他领导似的喊。
她于是推门进来。
或许是因为我先前有偷偷报告,所以做了心理准备,她没有按照我们计划中预想的那样,表现出惊愕的样子。或许她看到我的信息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猜到我们是在搞什么了?我不禁在心里猜测。
她毫不迟疑地走入,步伐和呼吸都没有停顿过一瞬。
那一刻,我知道无论我们准备了什么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了。
我惊愕地看着她。她在教室中间站定,用冷淡的眼神看了看他,又向上看了看我。我本不敢去看她,但被反将一军的愕然,驱使着我的眼睛,麻木地追随一切运动的物体,因此我和她对视上了。
对视的一瞬间,天地轰然倒错,连重力都逆转了。我坐在阶梯教室高高的椅子上,被站在地上的她,傲然地俯视着。我不禁瑟缩了,微微蜷在连排座椅里,像蜷在被告席中,仰视着她,等待她敲击木槌,断我的罪,判我的刑。
“这是你第二次背叛我了。”她冷冽的嗓音回荡在教室里。
他原本是打算先发制人地说那些他精心准备好的开场白的,此刻也像是和尚撞了钟,嗓子眼里的经文都哑了,腐烂了,流回到了肚子里。
我比他更加不敢说话。不过我也没什么要说的话,我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也不准备提起上诉,因此安静地等着她对我宣判就好了。
“我对你很失望,你没有恪守一个家臣应有的限度。”她说,“你不能诱导我放弃自己的勇气和热血,我有按我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权力,即使它并不是通俗功利角度上的最优解。”
我羞愧地挪开眼睛,胸腔里被抽了真空,心脏和肺皱缩起来,被她的话揉成一团,变成一副适合远远地扔进垃圾桶里的样子。
“这也不全是你的错。”她最终叹了口气,“你走吧,这件事是我们情侣之间的事,我们内部解决就好了。”
脚上的皮鞋很沉,我费尽全身力气,才将将能拖着它们,在教室的地面上蹭着向前。我默默拉开教室的后门,听到她的声音。
“我很伤心。”她说,“你选择了一个人作为权威,可那个人不是我。”
教室的隔音门在我身后关上。
# 17
我的胸腔里被强塞进一块燃红的炭,把我的心肝肺当成北京烤鸭一样又熏又烤。
她几天前的话,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无论是开组会,还是吃饭,又或者是躺在床上失眠,她的脸总是会浮现在眼前,既不愤怒,也不悲伤,只是平静地对我叙述那个事实——我又一次背叛了她。
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样了。他们会吵架吗?还是会冷战?会因此而分道扬镳吗?她会为此感到伤心还是愤怒?她一向很理智,思维也清晰,可是她先前已经被我背叛过一次爱情,如今又被他所伤害,她是否会因此而对爱情 PTSD 呢?是否会认为男人要么过于怂包,只想着被她征服,要么过于混蛋,只想着征服她呢?她会想起,在我们认识的初期,我曾和她讨论的,关于“男性基于权力结构来认知亲密关系”的话题吗?这话题会萦绕在她的心头,折磨她,让她对男人彻底失望吗?她会因此而往极端的方向靠近,变得不像原本的她吗?
如果她改变了,那我该继续追随她吗?这个想法突兀地出现在最后,吓了我一大跳。
我先前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忠诚。
紧接着,一个苦涩的想法做出了回答:没有人会要一个背叛了自己两次的家臣的。
我就这样伪装成选择已由她所作出的样子,逃避了对内心的审查。即使要痛苦地承认她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也比承认我自己的不忠要好。
我在信息真空中煎熬,又过了几天,我忍不住给她发消息。
“你们还好吗?”
这实在是一句相当狡猾的话。不仅是语气好像我是一个事件之外的朋友,在单纯地表达我的关心似的,而且还既可以解读为我是在问他们两个人的心理状态,又可以解读为我是在问她和他的关系是否还在延续。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呢?Mi amigo.”她讥讽地回复。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下意识地辩解。
她的消息连续传来。
“没关系哦~不用矜持啦~你是我的朋友,我当然愿意满足你的小心思,说些你想听到的话啦~”
“你想听‘我们很好,谢谢你的关心’是不是?我这就说给你听哦~”
“我们很好哦~谢谢你的关心!”
“满意了吗?截图保存下来,留着好好欣赏吧~”
“就这样把自己困在谎言里,然后幸福地去死吧~”
这条消息之后,她就拉黑了我。
我尝试给她打电话,打不通,又尝试她的其他联系方式,要么也被拉黑,要么没有回应。
我开始慌了,原本的侥幸心理,被一举砸了个粉碎。此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她陷入什么样的情绪,她都没有拉黑过我的联系方式。她是个无比重视沟通的人,可现在她却直接切断了所有沟通渠道。她一定是彻底对我失望了,认为对我连沟通的必要都没有了。
窗外在下大雨,我抄起雨伞,从研究生宿舍区一路跑到本科宿舍区,跑到她的宿舍楼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然不会有电影里那种巧合的情节,我没有正好撞到她出门,于是我站在斜对面的男生宿舍楼的屋檐下,紧盯着从女生宿舍楼出来的每一个人。
她会不会因为下雨而选择不出门呢?可是她的课排得很满,周六还有社团活动,周日是她唯一的休息日,她应该会想要冒着雨出来吧?
思绪纷乱得厉害,对被她彻底抛弃的恐惧支配着全部的意识。我焦躁地等待着,从中午开始一直等待,站得双腿发麻,膝盖板结成了一块硬邦邦的钢板,苦苦支撑着体重。
终于,傍晚的时候,我在密密麻麻的外卖员的缝隙中瞥见了她,她和她那个让我有些发怵的闺蜜一起走出来,打着伞往校外走去。我默默跟在后面,等到远离了宿舍,来到不至于引起骚动的大路上,我冲上前,拦在她们面前。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说。
“你……!”她抓紧她闺蜜的手。
她的闺蜜愣了一下,随即挂上坏笑,伏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雨声很大,我听不见。
“这样好吗?”她小声问。
她闺蜜鼓励地点头。
“好吧……”她咬一下嘴唇,转而面向我,“我会把你的 QQ 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你去校外开个房间,把房间号发给我,然后把手机关掉,跪着反思自己,我什么时候过去找你,你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是!谢谢主人!”我欣喜地说。
她没有回应我,只是拽着闺蜜,快步离开了。
我选了个有地毯的宾馆,关上门,把房号发给她,然后关机,跪在玄关,斜对着大门,等待她的到来。
最开始的感觉还好,只是跪着,到处看看。等感觉无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表,发现才过去了十几分钟。后腰和臀部的肌肉很累,我换成四肢着地地的跪法,很快又演变成用手肘撑着地面,额头顶在握拳的双手上的省力姿势。
空气很潮,我感觉很冷,脑子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每隔十几分钟就会确认一下时间。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很无聊,我想起人在上厕所没带手机的时候,会无聊到仔细阅读洗发水的配方表,但我连这个兴致都提不起来。
时间变成了一种刑具,我感觉我的精神在逐渐死亡,对时间流逝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了,只觉得很慢很慢。
就这样等了四个小时,将近十点钟的时候,门口终于想起了敲门声。我支起酸软的身体,跪着打开门,眼前出现了她被雨淋湿而发亮的粗跟短靴。
“反省得怎么样了?”她走进屋子,噗地一下坐到床上。
我膝行到她脚边,抬头仰视她:“我知道错了!我是你的家臣!我以后只遵从你的意志行事,不会再僭越,也不会再站在高处评价和审视你了!”
“还有呢?”她的语气没什么波动。
“呃……”我支支吾吾。
她随手扇我一耳光:“听好了,你是我一个人的奴隶,你不是什么‘家臣’,你是我的‘私臣’。我有时候会把你开放给我男朋友使用,不代表这个家的权威就是他,也不代表你能自己做出选择,擅自把他的优先级提到我之上。”
“是!”
这番大女主发言着实戳中我的 m 点,我恨不得长个尾巴出来摇,来告诉她我此刻的兴奋和崇拜。
“怎么跪了这么久还这么兴奋……”她跺跺脚,“都不知道这是在满足你,还是在惩罚你了。”
“是惩罚!绝对是惩罚!”我说。
“总之,我可以给你一次将功赎过的机会,但是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有一次背叛我的举动,那就永远拜拜。明白了吗?”
“绝对不会再有了!”我举三指发誓,“所以是什么机会啊?”
“简而言之,就是我要你帮我让他认识到,我和他是平等的,并且让他尊重我的主体性。”
“好的。”
“我已经有计划了,其实也不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你只需要坚持住,不喊安全词就好。”
她促狭地微笑起来。
时间是个比瓜田里的猹还要狡猾的小偷。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呢?是他不断表示想要她学习化妆的时候?是他在她面试前,非拉着她去买一双不舒服的高跟鞋的时候?是在他擅自买来符合男性审美的衣服,要她穿给她看的时候?还是每次她对未来有所规划,都被他以大创国奖得主的身份所劝退的时候?
我思来想去,想不明白。我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界限,一个足够大的事件,来解释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底是为什么,让事情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我察觉到的时候,一场没有铁幕演说的冷战早已在二人之间铺展开了,像夏夜森林中的磷火一样,安静地、冷酷地、幽灵似的燃烧着。
见面时,他们会下意识地绷紧身体,而这种紧绷很快就会发展成谈话中的对抗性态度,进而演变成敌意。但他们几乎不会争吵,最终结果基本上是以平静的散伙结束。可那并非真的平静,而是类似暴雨前夕,厚重的铅色的云凝在天上,让人的头发和汗毛都被头顶悬着的巨量电荷吸得竖立起来时,人所感受到的,庞大而无形的压力。
有什么东西在膨胀。就好像一个封闭的盒子里,装着两个气球,当气球膨胀起来的时候,盒子里的气压自然而然地就升高起来,压得人胸闷得喘不上气。
我当然能理解她为什么讨厌他的那些建议。他说的那些条条框框,在她看来不仅不符合女权主义的观念,过度迎合男权社会的规则和审美,而且存在着某种“改造”的意思:“我的能力在你之上,所以你要把我的建议奉为圭臬,削减自己的自由,按照我定下的金科玉律来改造自己。”她多半是这样解读的。
在我看来,他只是关心则乱,脑子里想说的建议太多了,再加上她的对抗性态度(人在受到反对时会愤怒,这是很正常的),说话的方式不自觉地变得直接了,说了不少直男发言,仅此而已。这算不得是什么错误,因为客观来看,他所说的东西确实基本都是对的,只是单纯的不符合她所崇尚的观念而已。
“他做过大创,拿过国奖,在路演和面试方面确实经验多些。虽然他说的那些大多都是学术圈的糟粕,是不良风气,但是这也确实是我国学术界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现状。”我如此劝慰她。
“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该放弃改变的努力。”她固执地说。
“这只是一厢情愿,力量弱小却还想着改变他人,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竹篮打水。”他立即反驳道。
“或许我们改天再商量这件事?”我打圆场。
于是一次次会面就这样在高度相似的沉默中解散。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明白我。”他愤愤地说,“我见过比赛圈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真的不是凭一个本科生就能改变的。”
“她多半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理解她吧。”我走在他并肩的位置,“她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情,很难对你说的那些产生共鸣。等她读研了,切身经历几次被抢一作二作,或者被导师要求把辛苦做完大半的项目让给师兄师弟的烂事,自然就会明白了。”
“到那时候就晚了,现在不赶紧努力的话,恐怕没法保 985 的研了。等到去了差学校再后知后觉地悔恨,那有什么用啊。”他说。
“倒也是。”我点点头。虽然我日子过得很佛系,但他们两个无疑是要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的。
“事到如今,我们两个必须联合起来了。”他说。
“怎么?”我问。
“我刚刚想了个计划,让她实际感受一次社会的黑暗,或许她就能正视现实了。”
“那很好啊,我扮演什么角色?”我走上前。
他停下脚步:“我要先声明,即使你参与进来,我也不会用平等的姿态和你共处,我依然会以男主人的身份命令你。”
“行。”我说。
他于是向我说了那个计划。
大胆,僭越,令人生畏。
# 16
简单来说,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她沉浸在一种“全能幻想”之中。她在想象中认为世界会按照她的命令而做出符合她心意的改变,但这只是她在全能自恋的视角下,对世界产生的扭曲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他打算安排一个适合辩论的场景,在模拟的情景中,用事实把她驳倒,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用真实的世界把她从全能自恋的镣铐中解救出来。
“所以我们搭建一个模拟的面试场景,让她体验一下刻薄的面试流程,感受一下科研圈子里的严肃压力,她应该就能认清现实了。”他站在讲台上,自信地说。
我有点犹豫,心里总觉得这有点过分了。但是面对着兴致勃勃的他,我也没法说出丧气的话来,只能嗯嗯啊啊地附和,不断点头,摆出完全听从他的调遣的样子。说到底,这是他们情侣之间的事情,轮不到我一个家臣来插手,我只要保持当个好用的工具就行了。
一周的时间里,我和他商量了具体的布置方案和简单的剧本,主体部分都是他提出的,我只增加一些边角的点缀。然后,按照计划,我去文印店做了一些桌牌之类的小道具,用来增加场景的真实感,他则去申请一间空教室作为场地。与此同时,由他去找她,半哄半骗地要她答应去参加一个“含金量很高的面试”。她不情不愿地同意了。
“今天可能会很难受,抱歉。”假面试的当天,我悄悄给她发消息。
她没有回复。
下午,我们在提前约好的教室等她。我坐在教室中后部,坐得很直,大脑像是收不到信号的电视屏幕,塞满了密密麻麻的噪点,喧闹成一片噪声的海洋,里面却没有任何内容。我的眼珠四处转动,企图发现哪怕一只在地上爬动的蚂蚁,能让我得以把无处安放的注意力寄托在它身上,可终究是徒劳无功,教室里什么也没有,我只能任由心脏在胸腔里从内而外地,像液压机一样地挤压我,把我挤扁成一个实心的垃圾块,方方正正地墩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他坐在教室第三排的位置,好整以暇地整理着西装,虽然只是在校门口商业街里的成衣店里买的工厂货,但他有着西服所最重要的配件——自信,在我看来,这便是一个足够耀眼的人了。
门外有人敲门。
“进!”他领导似的喊。
她于是推门进来。
或许是因为我先前有偷偷报告,所以做了心理准备,她没有按照我们计划中预想的那样,表现出惊愕的样子。或许她看到我的信息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猜到我们是在搞什么了?我不禁在心里猜测。
她毫不迟疑地走入,步伐和呼吸都没有停顿过一瞬。
那一刻,我知道无论我们准备了什么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了。
我惊愕地看着她。她在教室中间站定,用冷淡的眼神看了看他,又向上看了看我。我本不敢去看她,但被反将一军的愕然,驱使着我的眼睛,麻木地追随一切运动的物体,因此我和她对视上了。
对视的一瞬间,天地轰然倒错,连重力都逆转了。我坐在阶梯教室高高的椅子上,被站在地上的她,傲然地俯视着。我不禁瑟缩了,微微蜷在连排座椅里,像蜷在被告席中,仰视着她,等待她敲击木槌,断我的罪,判我的刑。
“这是你第二次背叛我了。”她冷冽的嗓音回荡在教室里。
他原本是打算先发制人地说那些他精心准备好的开场白的,此刻也像是和尚撞了钟,嗓子眼里的经文都哑了,腐烂了,流回到了肚子里。
我比他更加不敢说话。不过我也没什么要说的话,我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也不准备提起上诉,因此安静地等着她对我宣判就好了。
“我对你很失望,你没有恪守一个家臣应有的限度。”她说,“你不能诱导我放弃自己的勇气和热血,我有按我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权力,即使它并不是通俗功利角度上的最优解。”
我羞愧地挪开眼睛,胸腔里被抽了真空,心脏和肺皱缩起来,被她的话揉成一团,变成一副适合远远地扔进垃圾桶里的样子。
“这也不全是你的错。”她最终叹了口气,“你走吧,这件事是我们情侣之间的事,我们内部解决就好了。”
脚上的皮鞋很沉,我费尽全身力气,才将将能拖着它们,在教室的地面上蹭着向前。我默默拉开教室的后门,听到她的声音。
“我很伤心。”她说,“你选择了一个人作为权威,可那个人不是我。”
教室的隔音门在我身后关上。
# 17
我的胸腔里被强塞进一块燃红的炭,把我的心肝肺当成北京烤鸭一样又熏又烤。
她几天前的话,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无论是开组会,还是吃饭,又或者是躺在床上失眠,她的脸总是会浮现在眼前,既不愤怒,也不悲伤,只是平静地对我叙述那个事实——我又一次背叛了她。
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样了。他们会吵架吗?还是会冷战?会因此而分道扬镳吗?她会为此感到伤心还是愤怒?她一向很理智,思维也清晰,可是她先前已经被我背叛过一次爱情,如今又被他所伤害,她是否会因此而对爱情 PTSD 呢?是否会认为男人要么过于怂包,只想着被她征服,要么过于混蛋,只想着征服她呢?她会想起,在我们认识的初期,我曾和她讨论的,关于“男性基于权力结构来认知亲密关系”的话题吗?这话题会萦绕在她的心头,折磨她,让她对男人彻底失望吗?她会因此而往极端的方向靠近,变得不像原本的她吗?
如果她改变了,那我该继续追随她吗?这个想法突兀地出现在最后,吓了我一大跳。
我先前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忠诚。
紧接着,一个苦涩的想法做出了回答:没有人会要一个背叛了自己两次的家臣的。
我就这样伪装成选择已由她所作出的样子,逃避了对内心的审查。即使要痛苦地承认她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也比承认我自己的不忠要好。
我在信息真空中煎熬,又过了几天,我忍不住给她发消息。
“你们还好吗?”
这实在是一句相当狡猾的话。不仅是语气好像我是一个事件之外的朋友,在单纯地表达我的关心似的,而且还既可以解读为我是在问他们两个人的心理状态,又可以解读为我是在问她和他的关系是否还在延续。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呢?Mi amigo.”她讥讽地回复。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下意识地辩解。
她的消息连续传来。
“没关系哦~不用矜持啦~你是我的朋友,我当然愿意满足你的小心思,说些你想听到的话啦~”
“你想听‘我们很好,谢谢你的关心’是不是?我这就说给你听哦~”
“我们很好哦~谢谢你的关心!”
“满意了吗?截图保存下来,留着好好欣赏吧~”
“就这样把自己困在谎言里,然后幸福地去死吧~”
这条消息之后,她就拉黑了我。
我尝试给她打电话,打不通,又尝试她的其他联系方式,要么也被拉黑,要么没有回应。
我开始慌了,原本的侥幸心理,被一举砸了个粉碎。此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她陷入什么样的情绪,她都没有拉黑过我的联系方式。她是个无比重视沟通的人,可现在她却直接切断了所有沟通渠道。她一定是彻底对我失望了,认为对我连沟通的必要都没有了。
窗外在下大雨,我抄起雨伞,从研究生宿舍区一路跑到本科宿舍区,跑到她的宿舍楼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然不会有电影里那种巧合的情节,我没有正好撞到她出门,于是我站在斜对面的男生宿舍楼的屋檐下,紧盯着从女生宿舍楼出来的每一个人。
她会不会因为下雨而选择不出门呢?可是她的课排得很满,周六还有社团活动,周日是她唯一的休息日,她应该会想要冒着雨出来吧?
思绪纷乱得厉害,对被她彻底抛弃的恐惧支配着全部的意识。我焦躁地等待着,从中午开始一直等待,站得双腿发麻,膝盖板结成了一块硬邦邦的钢板,苦苦支撑着体重。
终于,傍晚的时候,我在密密麻麻的外卖员的缝隙中瞥见了她,她和她那个让我有些发怵的闺蜜一起走出来,打着伞往校外走去。我默默跟在后面,等到远离了宿舍,来到不至于引起骚动的大路上,我冲上前,拦在她们面前。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说。
“你……!”她抓紧她闺蜜的手。
她的闺蜜愣了一下,随即挂上坏笑,伏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雨声很大,我听不见。
“这样好吗?”她小声问。
她闺蜜鼓励地点头。
“好吧……”她咬一下嘴唇,转而面向我,“我会把你的 QQ 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你去校外开个房间,把房间号发给我,然后把手机关掉,跪着反思自己,我什么时候过去找你,你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是!谢谢主人!”我欣喜地说。
她没有回应我,只是拽着闺蜜,快步离开了。
我选了个有地毯的宾馆,关上门,把房号发给她,然后关机,跪在玄关,斜对着大门,等待她的到来。
最开始的感觉还好,只是跪着,到处看看。等感觉无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表,发现才过去了十几分钟。后腰和臀部的肌肉很累,我换成四肢着地地的跪法,很快又演变成用手肘撑着地面,额头顶在握拳的双手上的省力姿势。
空气很潮,我感觉很冷,脑子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每隔十几分钟就会确认一下时间。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很无聊,我想起人在上厕所没带手机的时候,会无聊到仔细阅读洗发水的配方表,但我连这个兴致都提不起来。
时间变成了一种刑具,我感觉我的精神在逐渐死亡,对时间流逝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了,只觉得很慢很慢。
就这样等了四个小时,将近十点钟的时候,门口终于想起了敲门声。我支起酸软的身体,跪着打开门,眼前出现了她被雨淋湿而发亮的粗跟短靴。
“反省得怎么样了?”她走进屋子,噗地一下坐到床上。
我膝行到她脚边,抬头仰视她:“我知道错了!我是你的家臣!我以后只遵从你的意志行事,不会再僭越,也不会再站在高处评价和审视你了!”
“还有呢?”她的语气没什么波动。
“呃……”我支支吾吾。
她随手扇我一耳光:“听好了,你是我一个人的奴隶,你不是什么‘家臣’,你是我的‘私臣’。我有时候会把你开放给我男朋友使用,不代表这个家的权威就是他,也不代表你能自己做出选择,擅自把他的优先级提到我之上。”
“是!”
这番大女主发言着实戳中我的 m 点,我恨不得长个尾巴出来摇,来告诉她我此刻的兴奋和崇拜。
“怎么跪了这么久还这么兴奋……”她跺跺脚,“都不知道这是在满足你,还是在惩罚你了。”
“是惩罚!绝对是惩罚!”我说。
“总之,我可以给你一次将功赎过的机会,但是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有一次背叛我的举动,那就永远拜拜。明白了吗?”
“绝对不会再有了!”我举三指发誓,“所以是什么机会啊?”
“简而言之,就是我要你帮我让他认识到,我和他是平等的,并且让他尊重我的主体性。”
“好的。”
“我已经有计划了,其实也不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你只需要坚持住,不喊安全词就好。”
她促狭地微笑起来。
Crying发布于 2026-01-27 00:07
Re: 【约稿】士(2026-01-26更新)
我最喜欢的人仿大大更新了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6-01-27 00:19
Re: Re: 【约稿】士(2026-01-26更新)

Sh
sheepsheep66发布于 2026-01-27 09:11
Re: 【约稿】士(2026-01-26更新)
支持写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