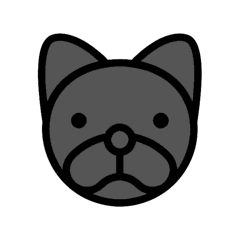瑪德琳·德·克萊蒙
阶级大小姐连载中原创虐杀高跟鞋骑人马现实鞋靴鞭打踩脸群体崇拜校园公开调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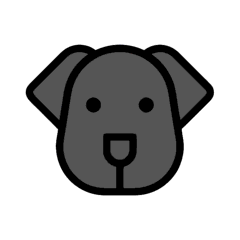
In
injustice_mirror发布于 2026-01-22 00:11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又更新了!昏迷十三次以后可以细说[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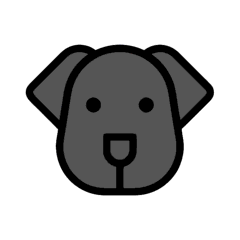
In
injustice_mirror发布于 2026-02-02 13:15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催更一下~另外誓约之履会有后续吗?
carpetman发布于 2026-02-08 19:34
Re: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injustice_mirror:↑催更一下~另外誓约之履会有后续吗?可以在人車競賽之前,插進一個番外篇。
生時服從,死時守護。
carpetman发布于 2026-02-08 19:35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第五小節:瑪德琳小姐的馬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本該是帝國前線最鋒利的劍。
在過去的歲月裡,只要他的戰馬踏上戰線,號角尚未吹響,士兵們的背脊便已挺直。那不是來自命令,而是來自一種近乎本能的信任——他來了,就不會輸。
帝國的軍報反覆出現過這個名字。
將領在作戰會議上提及時,語氣會不自覺放低。
士兵們在夜晚的營火旁,提到他時,總會先看一眼四周,像是在談論某種過於沉重、又過於神聖的存在。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
那是被寫進戰史的名字。
——「只要瓦爾克羅瓦還站著,戰線就不會崩。」
他曾單騎撕開敵軍側翼,血水混著雨水,馬蹄踏碎屍骸,硬生生將被包圍的第三軍團拖出死局。
他曾在暴雨傾盆的夜裡衝入敵陣,劍光一閃,敵軍的指揮旗桿在黑暗中折斷,戰場的秩序隨之一同瓦解。
他的衝鋒,意味著突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不會倒下的防線。
對無數士兵而言,他不是「勝利」。
他是活著的可能。
然而現在——
現在的他,站在聖蘭諾學院公爵區宿舍的入口。
不再披著戰甲。
不再握著染血的長劍。
甚至沒有坐在真正的戰馬背上。
他只是低頭站著,頸項微微前傾,肩線沉穩,姿態順從。
而他的身份,僅僅是——
瑪德琳小姐的「馬」。
公爵區宿舍入口的守衛,在聽到克萊蒙莊園大管家以一種冷靜、甚至帶著理所當然的語氣介紹時,整個人幾乎僵住了。
他原以為自己聽錯了。
又或者,是某個同名的侍從。
或者,是哪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玩笑。
可那張臉不可能認錯。
歲月與戰火在他身上留下痕跡,卻沒有磨損那份沉穩。眉骨、眼神、站姿——全都是戰場上千錘百鍊後才會有的東西。
守衛嚥了口口水,喉嚨乾得發痛。
「瓦爾克羅瓦大人……您為什麼會……」
他的語氣是敬的。
不是因為對方此刻的姿態。
而是因為那個名字本身,仍然帶著重量。
這個名字,曾讓敵軍退卻,曾讓戰線穩住,曾讓無數人在絕望中撐過一夜。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
守衛的話沒有說完。
因為羅蘭抬起了手。
動作很小,卻極其明確。
就像在戰場上示意「停止追擊」時一樣,無需多餘解釋。
「別那樣叫我。」
他的聲音平穩、低沉,沒有一絲顫抖。
沒有羞愧,沒有憤怒,甚至沒有自嘲。
就像他當年在滿是屍體的戰線上,冷靜地報出——
「右翼守住。」
一模一樣的語氣。
守衛的心臟狠狠一跳,像被什麼無形的東西攥緊。
「……那,閣下……」
他試圖換一個稱呼,卻發現沒有任何詞是合適的。
羅蘭沒有看他。
他的目光筆直地望向前方。
湖面反射著微光,風從水面吹來,帶著濕潤與寒意。
遠處傳來貴族學生的笑聲,輕快、無憂,與戰場上的嘶吼彷彿來自兩個世界。
那一瞬間,守衛忽然意識到——
這不是屈辱。
至少,對他而言不是。
羅蘭淡淡地開口,語氣平靜得近乎冷酷。
「戰場上,我守的是帝國。」
這句話,像是一段早已結束的歷史,被輕輕放下。
他頓了頓。
「現在,」
「我守的是她。」
羅蘭是在三個星期前,收到那封印著帝國內閣封蠟的信。
他沒有多想。
那時他正坐在駐地操場邊,慢慢擦拭長劍。天氣偏冷,北風裡帶著雪的氣味——北境最近確實不穩。邊軍斥候回報敵軍調動頻繁,軍需官已經開始提前調配補給。
這種時候,來自帝國中樞的信,只意味著一件事。
出征。
他甚至沒有立刻拆信。
只是把劍擦好,收入劍鞘,才回到營帳,在燈下坐定。
封蠟是帝國內閣紋章。
來自軍事統帥——克萊蒙公爵。
羅蘭的手,停了一瞬。
不是因為軍令。
而是因為那個姓氏。
他認得這個姓。
認得那座莊園。
也認得那座莊園裡——
那個曾站在玫瑰園階梯上,穿著淺藍色禮裙,笑得像午後陽光一樣明亮的小女孩。
他低頭,把封蠟折開。
信不是調兵令。
沒有軍陣圖。
沒有行軍路線。
內容簡單得近乎冷酷。
公爵大人最疼愛的女兒正在聖蘭諾學院。
她需要保護。
而學院規定,她只能帶一名奴隸與一名侍女前往——
卻沒有規定,可以帶幾匹「馬」。
人馬大賽即將開賽。她將參賽。
而他,可以以「奴隸」的身份,成為她的馬。
然後,留在她身邊。
羅蘭沒有動。
信紙在他手中,像雪一樣冷。
公爵知道這名騎士深愛著自己的女兒。
也知道他的身份,註定他永遠無法娶她,甚至不能正大光明地接近她。
於是,給了他一個機會。
不是榮耀。
不是軍功。
是一個——能陪在她身邊的人生。
信封裡還附著三樣東西:
一張放棄騎士身份的聲明。
一張奴隸契約。
以及,一枚銅錢。
那是他的賣身錢。
信的最後只有一句話——
若不願,此事從未存在。請焚信。
只要他點頭——
他的名字,會從軍報上消失。
他將不再屬於戰場。
不再屬於帝國軍籍。
他只會屬於——
她。
那裡有他打過的仗。
死去的戰友。
燃燒的城鎮。
他守住的邊境線。
他本該死在那裡。
或老去。
或成為傳說。
而不是——
牽著韁繩,站在一名少女面前,低頭,成為她的「馬」。
可他知道,這封信不是命令。
是詢問。
是某個人,在給他一個選擇。
他閉上眼。
想起很久以前。
那年她才十歲。
她站在馬廄外,踮著腳看他訓馬。
眼睛亮得不像貴族小姐,倒像個第一次看見世界的小孩。
她問過他一句話。
「騎士大人,馬會累嗎?」
他當時笑了。
「會。」
「那你呢?」
他沒有回答。
因為騎士不能說累。
——但他記住了。
這些年,他見過太多人把她當成「克萊蒙家的女兒」。
當成權力。
當成政治籌碼。
當成婚姻價值。
沒有人在意——
她會不會孤單。
會不會害怕。
會不會在深夜時,只是個年輕得不該承受那麼多目光的少女。
羅蘭睜開眼。
他忽然明白一件事。
在戰場上,他守的是帝國。
但她——
她從來沒有被任何人真正守過。
於是第二天,他上交軍印。
卸下軍銜。
留下長劍。
只帶走一樣東西。
她十歲那年,不小心掉在馬場裡的——
那條白色絲帶。
他一直留著。
瑪德琳視角
瑪德琳其實並不太記得他的名字。
她只記得菲利普告訴她——
父親為她送來了人馬競賽用的新馬。
僅此而已。
她站在宿舍入口的石階上。陽光落在她金色的髮絲上,細緻柔亮,像被精心梳理過的絲線。她微微偏著頭,打量著前方低頭站著的男人,目光坦率而專注——
那是一種評估的眼神。
就像在看一匹剛牽來的良駒。
她先注意到體格。
肩線穩。
背脊筆直。
頸項低垂的角度很漂亮。
——很好。
「比之前那匹好看多了。」
她輕聲說,語氣柔軟,像在挑選絲綢顏色。
她沒有意識到周圍安靜得不自然。
也沒有察覺守衛的臉色為什麼變得蒼白。
她只是自然地往前走了兩步,裙襬在石階上拖出細碎的聲響。
「抬頭。」
語氣不重,甚至稱得上溫和。
那是習慣被服從的人,才會有的語氣。
羅蘭抬起頭。
那一瞬間,她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
不是因為認出戰場傳說。
不是因為看見帝國的英雄。
只是因為——
「眼神很好。」
她滿意地點了點頭。
「夠安靜,也夠穩,不會亂動。」
她伸出戴著蕾絲手套的手指,輕輕托住他的下巴。動作自然,流暢,沒有任何遲疑——
像檢視馬匹牙口一樣自然。
她的手很小,也很輕。
可那個動作,沒有一絲猶豫。
「父親果然懂我。」
她露出笑容。
那笑容甜得近乎天真。
「我不喜歡會掙扎的。」
風從湖面吹來,帶著微涼的濕意,掠過她的髮絲。她的神情終於變得真正愉快——像孩子拿到最心儀的玩具時那樣單純。
「這匹,應該很乖吧?」
她看向大管家,語氣甚至帶著一點期待。
在她的世界裡,沒有戰史。
沒有功績。
沒有那句——「只要他還站著,戰線就不會崩」。
只有——
順不順手。
聽不聽話。
好不好看。
她再次看向羅蘭,語氣輕得像羽毛落下。
「從今天開始,你就是我的了。」
不是命令。
是對物品的宣告所有權。
然後她轉身,裙襬旋開柔軟的弧線。
「牽進來吧。」
就像在說——
把馬帶進馬廄。
而她的心情,很好。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本該是帝國前線最鋒利的劍。
在過去的歲月裡,只要他的戰馬踏上戰線,號角尚未吹響,士兵們的背脊便已挺直。那不是來自命令,而是來自一種近乎本能的信任——他來了,就不會輸。
帝國的軍報反覆出現過這個名字。
將領在作戰會議上提及時,語氣會不自覺放低。
士兵們在夜晚的營火旁,提到他時,總會先看一眼四周,像是在談論某種過於沉重、又過於神聖的存在。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
那是被寫進戰史的名字。
——「只要瓦爾克羅瓦還站著,戰線就不會崩。」
他曾單騎撕開敵軍側翼,血水混著雨水,馬蹄踏碎屍骸,硬生生將被包圍的第三軍團拖出死局。
他曾在暴雨傾盆的夜裡衝入敵陣,劍光一閃,敵軍的指揮旗桿在黑暗中折斷,戰場的秩序隨之一同瓦解。
他的衝鋒,意味著突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不會倒下的防線。
對無數士兵而言,他不是「勝利」。
他是活著的可能。
然而現在——
現在的他,站在聖蘭諾學院公爵區宿舍的入口。
不再披著戰甲。
不再握著染血的長劍。
甚至沒有坐在真正的戰馬背上。
他只是低頭站著,頸項微微前傾,肩線沉穩,姿態順從。
而他的身份,僅僅是——
瑪德琳小姐的「馬」。
公爵區宿舍入口的守衛,在聽到克萊蒙莊園大管家以一種冷靜、甚至帶著理所當然的語氣介紹時,整個人幾乎僵住了。
他原以為自己聽錯了。
又或者,是某個同名的侍從。
或者,是哪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玩笑。
可那張臉不可能認錯。
歲月與戰火在他身上留下痕跡,卻沒有磨損那份沉穩。眉骨、眼神、站姿——全都是戰場上千錘百鍊後才會有的東西。
守衛嚥了口口水,喉嚨乾得發痛。
「瓦爾克羅瓦大人……您為什麼會……」
他的語氣是敬的。
不是因為對方此刻的姿態。
而是因為那個名字本身,仍然帶著重量。
這個名字,曾讓敵軍退卻,曾讓戰線穩住,曾讓無數人在絕望中撐過一夜。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
守衛的話沒有說完。
因為羅蘭抬起了手。
動作很小,卻極其明確。
就像在戰場上示意「停止追擊」時一樣,無需多餘解釋。
「別那樣叫我。」
他的聲音平穩、低沉,沒有一絲顫抖。
沒有羞愧,沒有憤怒,甚至沒有自嘲。
就像他當年在滿是屍體的戰線上,冷靜地報出——
「右翼守住。」
一模一樣的語氣。
守衛的心臟狠狠一跳,像被什麼無形的東西攥緊。
「……那,閣下……」
他試圖換一個稱呼,卻發現沒有任何詞是合適的。
羅蘭沒有看他。
他的目光筆直地望向前方。
湖面反射著微光,風從水面吹來,帶著濕潤與寒意。
遠處傳來貴族學生的笑聲,輕快、無憂,與戰場上的嘶吼彷彿來自兩個世界。
那一瞬間,守衛忽然意識到——
這不是屈辱。
至少,對他而言不是。
羅蘭淡淡地開口,語氣平靜得近乎冷酷。
「戰場上,我守的是帝國。」
這句話,像是一段早已結束的歷史,被輕輕放下。
他頓了頓。
「現在,」
「我守的是她。」
羅蘭是在三個星期前,收到那封印著帝國內閣封蠟的信。
他沒有多想。
那時他正坐在駐地操場邊,慢慢擦拭長劍。天氣偏冷,北風裡帶著雪的氣味——北境最近確實不穩。邊軍斥候回報敵軍調動頻繁,軍需官已經開始提前調配補給。
這種時候,來自帝國中樞的信,只意味著一件事。
出征。
他甚至沒有立刻拆信。
只是把劍擦好,收入劍鞘,才回到營帳,在燈下坐定。
封蠟是帝國內閣紋章。
來自軍事統帥——克萊蒙公爵。
羅蘭的手,停了一瞬。
不是因為軍令。
而是因為那個姓氏。
他認得這個姓。
認得那座莊園。
也認得那座莊園裡——
那個曾站在玫瑰園階梯上,穿著淺藍色禮裙,笑得像午後陽光一樣明亮的小女孩。
他低頭,把封蠟折開。
信不是調兵令。
沒有軍陣圖。
沒有行軍路線。
內容簡單得近乎冷酷。
公爵大人最疼愛的女兒正在聖蘭諾學院。
她需要保護。
而學院規定,她只能帶一名奴隸與一名侍女前往——
卻沒有規定,可以帶幾匹「馬」。
人馬大賽即將開賽。她將參賽。
而他,可以以「奴隸」的身份,成為她的馬。
然後,留在她身邊。
羅蘭沒有動。
信紙在他手中,像雪一樣冷。
公爵知道這名騎士深愛著自己的女兒。
也知道他的身份,註定他永遠無法娶她,甚至不能正大光明地接近她。
於是,給了他一個機會。
不是榮耀。
不是軍功。
是一個——能陪在她身邊的人生。
信封裡還附著三樣東西:
一張放棄騎士身份的聲明。
一張奴隸契約。
以及,一枚銅錢。
那是他的賣身錢。
信的最後只有一句話——
若不願,此事從未存在。請焚信。
只要他點頭——
他的名字,會從軍報上消失。
他將不再屬於戰場。
不再屬於帝國軍籍。
他只會屬於——
她。
那裡有他打過的仗。
死去的戰友。
燃燒的城鎮。
他守住的邊境線。
他本該死在那裡。
或老去。
或成為傳說。
而不是——
牽著韁繩,站在一名少女面前,低頭,成為她的「馬」。
可他知道,這封信不是命令。
是詢問。
是某個人,在給他一個選擇。
他閉上眼。
想起很久以前。
那年她才十歲。
她站在馬廄外,踮著腳看他訓馬。
眼睛亮得不像貴族小姐,倒像個第一次看見世界的小孩。
她問過他一句話。
「騎士大人,馬會累嗎?」
他當時笑了。
「會。」
「那你呢?」
他沒有回答。
因為騎士不能說累。
——但他記住了。
這些年,他見過太多人把她當成「克萊蒙家的女兒」。
當成權力。
當成政治籌碼。
當成婚姻價值。
沒有人在意——
她會不會孤單。
會不會害怕。
會不會在深夜時,只是個年輕得不該承受那麼多目光的少女。
羅蘭睜開眼。
他忽然明白一件事。
在戰場上,他守的是帝國。
但她——
她從來沒有被任何人真正守過。
於是第二天,他上交軍印。
卸下軍銜。
留下長劍。
只帶走一樣東西。
她十歲那年,不小心掉在馬場裡的——
那條白色絲帶。
他一直留著。
瑪德琳視角
瑪德琳其實並不太記得他的名字。
她只記得菲利普告訴她——
父親為她送來了人馬競賽用的新馬。
僅此而已。
她站在宿舍入口的石階上。陽光落在她金色的髮絲上,細緻柔亮,像被精心梳理過的絲線。她微微偏著頭,打量著前方低頭站著的男人,目光坦率而專注——
那是一種評估的眼神。
就像在看一匹剛牽來的良駒。
她先注意到體格。
肩線穩。
背脊筆直。
頸項低垂的角度很漂亮。
——很好。
「比之前那匹好看多了。」
她輕聲說,語氣柔軟,像在挑選絲綢顏色。
她沒有意識到周圍安靜得不自然。
也沒有察覺守衛的臉色為什麼變得蒼白。
她只是自然地往前走了兩步,裙襬在石階上拖出細碎的聲響。
「抬頭。」
語氣不重,甚至稱得上溫和。
那是習慣被服從的人,才會有的語氣。
羅蘭抬起頭。
那一瞬間,她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
不是因為認出戰場傳說。
不是因為看見帝國的英雄。
只是因為——
「眼神很好。」
她滿意地點了點頭。
「夠安靜,也夠穩,不會亂動。」
她伸出戴著蕾絲手套的手指,輕輕托住他的下巴。動作自然,流暢,沒有任何遲疑——
像檢視馬匹牙口一樣自然。
她的手很小,也很輕。
可那個動作,沒有一絲猶豫。
「父親果然懂我。」
她露出笑容。
那笑容甜得近乎天真。
「我不喜歡會掙扎的。」
風從湖面吹來,帶著微涼的濕意,掠過她的髮絲。她的神情終於變得真正愉快——像孩子拿到最心儀的玩具時那樣單純。
「這匹,應該很乖吧?」
她看向大管家,語氣甚至帶著一點期待。
在她的世界裡,沒有戰史。
沒有功績。
沒有那句——「只要他還站著,戰線就不會崩」。
只有——
順不順手。
聽不聽話。
好不好看。
她再次看向羅蘭,語氣輕得像羽毛落下。
「從今天開始,你就是我的了。」
不是命令。
是對物品的宣告所有權。
然後她轉身,裙襬旋開柔軟的弧線。
「牽進來吧。」
就像在說——
把馬帶進馬廄。
而她的心情,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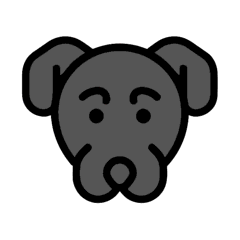
Li
littlelittlepet发布于 2026-02-08 21:09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好看啊,可以感覺得到作者其實研究過不少這方面的知識啊
福莱沃博士发布于 2026-02-15 15:47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期待接下来的人马大赛,罗兰接下来会作为骑乘马还是拉车马?这个角色会常驻吗?
carpetman发布于 2026-02-16 22:54
Re: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littlelittlepet:↑好看啊,可以感覺得到作者其實研究過不少這方面的知識啊謝謝。
carpetman发布于 2026-02-16 22:55
Re: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carpetman发布于 ,编辑于 2026-02-17 20:58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第六小節 人車大賽(上)
在聖蘭諾學院(Saint Lannor Academy),新生入學的第一場儀式——
不是授徽,不是宣誓。
而是——
人車大賽
這是一場既優雅、又危險的競技。
一場專屬於高貴血統的試煉。
一場將「統御」與「殘酷」同時公開於陽光之下的展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黑石之環
賽事於學院中央的競技之環舉行——仿若縮小版的 Circus Maximus。
黑色石道由湖畔一路鋪展而來,筆直延伸,在兩端收束為巨大的石製轉角。
中央立著長形分隔牆,牆上懸掛各家族旗幟。金線繡成的紋章在湖風中翻飛,獅、鷹、百合與飛龍彼此對望,如同無聲的宣戰。
石牆上嵌著計圈的銀製標記,每完成一圈,便由侍從翻動。
七枚圓盤,如同七次審判。
看台以黑石砌成,層層遞高。
席位依血統與爵位分區——
越接近中央高座,血統越純粹,權力越集中。
高座之上,皇帝與皇室親臨。
伯爵以上的貴族幾乎全數受邀。
公爵席位以金色欄杆分隔,伯爵席以銀線區分。
子爵與男爵,往往只能苦求一張邊緣席位,遠遠望著中央。
觀禮者只有學生與貴族。
沒有平民的喧嘩,沒有商販的叫賣。
連掌聲都帶著節制。
這不是娛樂。
這是——
血統之間的較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色御車
賽場上懸掛四面大旗:
• 純白(Alba)
• 蒼藍(Veneta)
• 深紅(Russata)
• 翡翠(Prasina)
每一色,由一名新生貴族小姐擔任車手。
她們身著和車隊同色華麗長裙。
裙襬層層堆疊,絲緞在陽光下泛起柔光,刺繡描繪家族歷史。
腰間佩著家徽,髮間鑲嵌寶石與珍珠。
腳踏華麗的絲綢高跟鞋,
白色手套之中,握著長鞭。
她們站在輕巧而精緻的御車之上,
背脊挺直,神情從容。
彷彿只是出席一場舞會。
腳下的並非賽道——
而是她們的舞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名「人馬」
為保證小姐們的安全,牽引御車的並非馬匹。
而是四名奴隸。
他們佩戴金屬頸環與皮革束帶,
繩索自腰部延伸至車架,
肌肉繃緊如繩索本身。
背部裸露,
便於主人鞭策。
這些人並非隨意挑選。
每一名小姐的父親,
會派出最忠誠、最強壯、最願為主人赴死的心腹。
有的是家族私軍的舊兵。
有的是自幼訓練的專屬護衛。
有的是曾為主人擋刀的死士。
因為這場比賽,雖明令禁止「沉船事故(naufragium)」——
卻從不真正安全。
賽道兩端設有巨大石柱轉角。
石柱底部被磨得光滑發亮。
學生們私下稱之為——
彎月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彎月角的瞬間
真正的考驗在轉彎。
四名人馬必須步調一致。
呼吸、步頻、力量——
只要稍有錯亂,御車便會傾斜。
那一瞬間,
忠誠被推至極限。
有人咬牙拉緊繩索,讓肩骨幾乎錯位。
有人強行扭轉身體,以自身為軸穩住車架。
有人乾脆撲倒在地,用背脊抵住車輪,換取半秒的平衡。
骨骼可能折裂。
肩膀可能脫臼。
腳踝可能瞬間錯位。
即使其中一人、甚至數人脫落,
只要車身未翻——
御車仍可前進。
比賽仍可繼續。
這裡競爭尤其激烈。
小姐們的長鞭,往往在此處「失控」。
一記「誤抽」,足以讓對手人馬步伐紊亂。
彎月角的一個小小「意外」,
可能讓整隊失去節奏。
一個呼吸的遲疑,
便決定勝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干擾的藝術
這不是單純的速度較量。
小姐們手中的長鞭——
既是驅使,也是威懾。
她們可以:
• 催促自己的奴隸加速
• 將鞭尾揮向對手奴隸
• 擾亂步伐
• 迫使對方偏離內線
規則明文禁止攻擊車手。
但對「人馬」的干擾,界線模糊。
有時,小手一滑。
鞭尾不慎落在膝後。
或抽在腰側。
甚至掠過更為脆弱的部位。
若角度拿捏得當——
那只是「比賽意外」。
干擾是一門分寸的學問。
太狠,會被舉旗警告。
太柔,會失去勝利。
看台之上,賠率隨每一次鞭聲變動。
貴族低聲交談。
學生默默觀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圈規則
比賽延續古法,以七圈決定勝負。
但往往——
第一圈,人馬們已略顯失衡。
第二圈,背上鞭痕縱橫。
第三圈,呼吸開始凌亂。
因此,比賽允許更換牽引用的人馬。
一場比賽,通常需要更換三次牽引。
每隊:
• 起始四人
• 第三圈替換四人
• 第五或第六圈再換四人
共計十二人。
四支隊伍,
一場比賽便動用四十八人。
為了優雅與秩序,大賽嚴禁攻擊車手。
嚴禁蓄意製造沉船事故。
卻從未給予人馬們任何保護。
只要御車未翻。
只要小姐未傷。
便可被稱為——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後一圈
第七圈。
鞭聲更加急促。
人馬的牙縫間滲出血沫。
皮膚早已布滿鞭痕。
汗水與血水混合,順著脊背流淌。
他們的視線開始模糊。
腳步卻不能停。
御車之上,小姐們依舊優雅。
她們甚至沒有流汗。
她們只需——
揮鞭。
催促。
逼迫。
榨乾最後一絲力氣。
直到終點旗落下。
塵土緩緩沉降。
弦樂與銅管交織的莊嚴旋律響起。
高座之上,皇帝與皇室起身致意。
伯爵以上的貴族彼此交換目光。
有人歡喜。
有人沉默。
有人贏錢。
有人失算。
然後——
數名奴隸將領獎台搬至賽道中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獎台上的光芒
踩著跪伏的奴隸作為踏階。
四名新生小姐依序走下御車。
將手中的長鞭交給侍女。
前三名踏上高低分明的階梯。
第四名獲得象徵性的徽章與皇室的點頭。
她們依舊光彩照人。
長裙雖微沾塵土,
卻在侍女的巧手下迅速恢復完美弧度。
胸前家徽閃耀。
臉上帶著微喘與紅暈——
如同剛完成一場舞會。
她們從未跌落。
從未被攻擊。
從未倒地。
承受風險與衝擊的,
永遠是繩索前端的人。
只要沒有沉船事故。
或者即將事故時,奴隸及時犧牲護主。
她們便可以輕聲笑談:
「妳第六圈的內線太貪心了。」
「那一鞭只是提醒。」
「下次我會晚半拍再換人。」
語氣輕鬆。
甚至帶著少女的俏皮。
觀禮席上,她們的父親滿意頷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圈的代價
而賽道另一端——
畫面截然不同。
按統計,
參賽的四十八名奴隸,
多數不會在下一次比賽再度出現。
代價並不僅來自極限奔跑。
更多時候——
來自背後的長鞭。
來自彎月角的犧牲。
有人在彎角用身體撐住傾斜車架,脊椎粉碎。
有人在補給區被拖走時已無意識。
有人在最後衝刺時吐血仍咬牙前行,直到力竭倒地。
規則禁止沉船事故。
卻未禁止耗盡生命。
只要車未翻。
小姐未傷。
比賽便被視為成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染紅的長鞭
小姐們手中的長鞭,是這場大賽最華麗的道具。
鑲金絨面手柄嵌著寶石,握感柔軟,保護她們細緻的小手。
而鞭身卻截然不同——
鋼絲與牛筋纏繞,柔韌而冷酷。
只需最小的力氣,
便能給人馬最大的「激勵」。
她們從未吝嗇使用。
那鞭子曾落在:
自己奴隸的——
• 背部
• 大腿
• 腹側
也曾落在他人奴隸的——
• 關節後方
• 面部
• 更加脆弱的地方
或為加速。
或為干擾。
或為勝利。
第五圈後,
鞭身往往已被徹底染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記憶與遺忘
夜色降臨。
小姐們在宴會廳中交談。
燭光映照珠寶。
弦樂聲輕柔流淌。
貴族誇讚她們的優雅。
皇室評估她們的未來。
而那十二名奴隸——
她們通常不記得名字。
她們記得的只有:
「父親準備的第三組比較穩。」
「可惜第五號沒撐住。」
「最後那組不夠耐久。」
湖面靜如鏡面。
優雅仍在延續。
而賽道上的一切——
已被清理乾淨。
在聖蘭諾學院(Saint Lannor Academy),新生入學的第一場儀式——
不是授徽,不是宣誓。
而是——
人車大賽
這是一場既優雅、又危險的競技。
一場專屬於高貴血統的試煉。
一場將「統御」與「殘酷」同時公開於陽光之下的展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黑石之環
賽事於學院中央的競技之環舉行——仿若縮小版的 Circus Maximus。
黑色石道由湖畔一路鋪展而來,筆直延伸,在兩端收束為巨大的石製轉角。
中央立著長形分隔牆,牆上懸掛各家族旗幟。金線繡成的紋章在湖風中翻飛,獅、鷹、百合與飛龍彼此對望,如同無聲的宣戰。
石牆上嵌著計圈的銀製標記,每完成一圈,便由侍從翻動。
七枚圓盤,如同七次審判。
看台以黑石砌成,層層遞高。
席位依血統與爵位分區——
越接近中央高座,血統越純粹,權力越集中。
高座之上,皇帝與皇室親臨。
伯爵以上的貴族幾乎全數受邀。
公爵席位以金色欄杆分隔,伯爵席以銀線區分。
子爵與男爵,往往只能苦求一張邊緣席位,遠遠望著中央。
觀禮者只有學生與貴族。
沒有平民的喧嘩,沒有商販的叫賣。
連掌聲都帶著節制。
這不是娛樂。
這是——
血統之間的較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色御車
賽場上懸掛四面大旗:
• 純白(Alba)
• 蒼藍(Veneta)
• 深紅(Russata)
• 翡翠(Prasina)
每一色,由一名新生貴族小姐擔任車手。
她們身著和車隊同色華麗長裙。
裙襬層層堆疊,絲緞在陽光下泛起柔光,刺繡描繪家族歷史。
腰間佩著家徽,髮間鑲嵌寶石與珍珠。
腳踏華麗的絲綢高跟鞋,
白色手套之中,握著長鞭。
她們站在輕巧而精緻的御車之上,
背脊挺直,神情從容。
彷彿只是出席一場舞會。
腳下的並非賽道——
而是她們的舞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名「人馬」
為保證小姐們的安全,牽引御車的並非馬匹。
而是四名奴隸。
他們佩戴金屬頸環與皮革束帶,
繩索自腰部延伸至車架,
肌肉繃緊如繩索本身。
背部裸露,
便於主人鞭策。
這些人並非隨意挑選。
每一名小姐的父親,
會派出最忠誠、最強壯、最願為主人赴死的心腹。
有的是家族私軍的舊兵。
有的是自幼訓練的專屬護衛。
有的是曾為主人擋刀的死士。
因為這場比賽,雖明令禁止「沉船事故(naufragium)」——
卻從不真正安全。
賽道兩端設有巨大石柱轉角。
石柱底部被磨得光滑發亮。
學生們私下稱之為——
彎月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彎月角的瞬間
真正的考驗在轉彎。
四名人馬必須步調一致。
呼吸、步頻、力量——
只要稍有錯亂,御車便會傾斜。
那一瞬間,
忠誠被推至極限。
有人咬牙拉緊繩索,讓肩骨幾乎錯位。
有人強行扭轉身體,以自身為軸穩住車架。
有人乾脆撲倒在地,用背脊抵住車輪,換取半秒的平衡。
骨骼可能折裂。
肩膀可能脫臼。
腳踝可能瞬間錯位。
即使其中一人、甚至數人脫落,
只要車身未翻——
御車仍可前進。
比賽仍可繼續。
這裡競爭尤其激烈。
小姐們的長鞭,往往在此處「失控」。
一記「誤抽」,足以讓對手人馬步伐紊亂。
彎月角的一個小小「意外」,
可能讓整隊失去節奏。
一個呼吸的遲疑,
便決定勝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干擾的藝術
這不是單純的速度較量。
小姐們手中的長鞭——
既是驅使,也是威懾。
她們可以:
• 催促自己的奴隸加速
• 將鞭尾揮向對手奴隸
• 擾亂步伐
• 迫使對方偏離內線
規則明文禁止攻擊車手。
但對「人馬」的干擾,界線模糊。
有時,小手一滑。
鞭尾不慎落在膝後。
或抽在腰側。
甚至掠過更為脆弱的部位。
若角度拿捏得當——
那只是「比賽意外」。
干擾是一門分寸的學問。
太狠,會被舉旗警告。
太柔,會失去勝利。
看台之上,賠率隨每一次鞭聲變動。
貴族低聲交談。
學生默默觀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圈規則
比賽延續古法,以七圈決定勝負。
但往往——
第一圈,人馬們已略顯失衡。
第二圈,背上鞭痕縱橫。
第三圈,呼吸開始凌亂。
因此,比賽允許更換牽引用的人馬。
一場比賽,通常需要更換三次牽引。
每隊:
• 起始四人
• 第三圈替換四人
• 第五或第六圈再換四人
共計十二人。
四支隊伍,
一場比賽便動用四十八人。
為了優雅與秩序,大賽嚴禁攻擊車手。
嚴禁蓄意製造沉船事故。
卻從未給予人馬們任何保護。
只要御車未翻。
只要小姐未傷。
便可被稱為——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後一圈
第七圈。
鞭聲更加急促。
人馬的牙縫間滲出血沫。
皮膚早已布滿鞭痕。
汗水與血水混合,順著脊背流淌。
他們的視線開始模糊。
腳步卻不能停。
御車之上,小姐們依舊優雅。
她們甚至沒有流汗。
她們只需——
揮鞭。
催促。
逼迫。
榨乾最後一絲力氣。
直到終點旗落下。
塵土緩緩沉降。
弦樂與銅管交織的莊嚴旋律響起。
高座之上,皇帝與皇室起身致意。
伯爵以上的貴族彼此交換目光。
有人歡喜。
有人沉默。
有人贏錢。
有人失算。
然後——
數名奴隸將領獎台搬至賽道中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獎台上的光芒
踩著跪伏的奴隸作為踏階。
四名新生小姐依序走下御車。
將手中的長鞭交給侍女。
前三名踏上高低分明的階梯。
第四名獲得象徵性的徽章與皇室的點頭。
她們依舊光彩照人。
長裙雖微沾塵土,
卻在侍女的巧手下迅速恢復完美弧度。
胸前家徽閃耀。
臉上帶著微喘與紅暈——
如同剛完成一場舞會。
她們從未跌落。
從未被攻擊。
從未倒地。
承受風險與衝擊的,
永遠是繩索前端的人。
只要沒有沉船事故。
或者即將事故時,奴隸及時犧牲護主。
她們便可以輕聲笑談:
「妳第六圈的內線太貪心了。」
「那一鞭只是提醒。」
「下次我會晚半拍再換人。」
語氣輕鬆。
甚至帶著少女的俏皮。
觀禮席上,她們的父親滿意頷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圈的代價
而賽道另一端——
畫面截然不同。
按統計,
參賽的四十八名奴隸,
多數不會在下一次比賽再度出現。
代價並不僅來自極限奔跑。
更多時候——
來自背後的長鞭。
來自彎月角的犧牲。
有人在彎角用身體撐住傾斜車架,脊椎粉碎。
有人在補給區被拖走時已無意識。
有人在最後衝刺時吐血仍咬牙前行,直到力竭倒地。
規則禁止沉船事故。
卻未禁止耗盡生命。
只要車未翻。
小姐未傷。
比賽便被視為成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染紅的長鞭
小姐們手中的長鞭,是這場大賽最華麗的道具。
鑲金絨面手柄嵌著寶石,握感柔軟,保護她們細緻的小手。
而鞭身卻截然不同——
鋼絲與牛筋纏繞,柔韌而冷酷。
只需最小的力氣,
便能給人馬最大的「激勵」。
她們從未吝嗇使用。
那鞭子曾落在:
自己奴隸的——
• 背部
• 大腿
• 腹側
也曾落在他人奴隸的——
• 關節後方
• 面部
• 更加脆弱的地方
或為加速。
或為干擾。
或為勝利。
第五圈後,
鞭身往往已被徹底染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記憶與遺忘
夜色降臨。
小姐們在宴會廳中交談。
燭光映照珠寶。
弦樂聲輕柔流淌。
貴族誇讚她們的優雅。
皇室評估她們的未來。
而那十二名奴隸——
她們通常不記得名字。
她們記得的只有:
「父親準備的第三組比較穩。」
「可惜第五號沒撐住。」
「最後那組不夠耐久。」
湖面靜如鏡面。
優雅仍在延續。
而賽道上的一切——
已被清理乾淨。
福莱沃博士发布于 2026-02-17 00:02
Re: Re: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carpetman发布于 ,编辑于 2026-02-17 21:07
Re: Re: Re: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carpetman发布于 2026-02-17 21:02
Re: 瑪德琳·德·克萊蒙
人車大賽(外傳)
紅方——羅蘭伯爵小姐
賽場中央,深紅色的大旗在湖風中獵獵作響。
那不是明亮的紅。
而是近乎酒色的深紅——厚重、濃烈,像歷史沉澱後的血與榮耀。
羅蘭伯爵小姐站在御車之上,指尖微微收緊。
她的裙裝以紅絲緞為底,邊緣以黑金細線繡出家族的狼紋徽章。狼頭低伏,目光銳利——象徵她們家族自北境荒原崛起的歷史。
紅寶石耳墜隨風輕晃,映著陽光,折射出微小卻鋒利的光點。
她的姿態優雅,背脊筆直,肩線穩定。
從看台遠望,沒有人能察覺她此刻心底翻湧的情緒。
在這場人馬大賽中,她既沒有克萊蒙公國那樣的底蘊,也沒有西勒斯公國那樣的商業傳承。
更何況——
那一位。
皇帝第一公主——夏洛特殿下。
羅蘭伯爵小姐輕輕吐出一口氣。
她不是天真少女。
她很清楚這場比賽真正比拼的是什麼。
不是速度。
不是技巧。
而是——背後的力量。
她的父親,羅蘭伯爵,領地廣闊,邊境穩固,家族歷史超過三百年。
在地方議會中,他說話仍有分量。
在北境,他的軍隊仍然令人敬畏。
但在聖蘭諾學院這樣的舞台——
公爵與王族的陰影太過巨大。
伯爵府的書房燭火搖曳。
父親站在窗前,背對著她。
「紅方不好跑。」他低聲說。
她沒有回答。
「我們準備了三組牽引。」
「第一組是舊軍士,穩。」
「第二組是你叔父親自挑的,爆發力強。」
「第三組……」他停了一下,「……他們撐不了太久,但夠拼命。」
她知道那句話的意思。
夠拼命。
在這場賽事裡,那意味著什麼,她比誰都清楚。
她沒有哭,也沒有抱怨。
只是輕聲說:「我會讓他們跑得值得。」
那一瞬間,她看見父親眼裡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驕傲。
擔憂。
還有無法言說的現實。
因為他知道——
她注定不是這場盛宴的主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賽場上,四組人馬已就位。
紅方的第一組站在她腳下。
四名男人,肩寬背闊,腰部束帶繃緊。
他們的皮膚因長年軍旅而略帶粗糙,肌肉線條清晰。
其中兩人臉上仍留有舊戰傷的痕跡。
她認得他們。
那是父親舊部。
他們曾在邊境守夜,曾為家族擋過流箭。
如今,他們低頭站在她面前,頸環在陽光下泛著金屬光澤。
她的喉嚨微微發緊。
她必須駕馭他們。
否則,他們的犧牲只會成為笑話。
紅旗在風中翻動。
她抬起手,白手套包覆著纖細的手指。
長鞭在陽光下閃過一抹冷光。
她並不喜歡鞭子。
她練習過很多次。
但每一次落下,手腕都會不自覺遲疑。
不像公爵家的小姐們,那樣自然。
不像王女那樣毫無動搖。
她知道自己會是配角。
這時,一道極輕的腳步聲自車後傳來。
她的侍女——莉亞——靠近一步,俯身,聲音幾乎被風吞沒。
「小姐……」
她沒有回頭,只是微微側耳。
「克萊蒙家的頭馬……」
莉亞停了一下,像在斟酌用詞。
「是羅蘭大人。」
風忽然變得很冷。
她的指尖猛地收緊。
絲緞被捏出一道深深的摺痕。
「……哪位羅蘭?」
她的聲音仍舊平穩。
侍女的喉嚨滾動了一下。
「瓦爾克羅瓦大人。」
那一瞬間,賽場的聲音彷彿全部遠去。
銅管聲、學生低語、旗幟翻動——
全部被抽離。
她聽見的只有自己的心跳。
羅蘭。
那個名字,對她而言,從來不是普通的軍報字眼。
她年幼時曾站在父親書房外,偷聽將軍們談話。
那個名字反覆出現——
「只要瓦爾克羅瓦還站著,戰線就不會崩。」
她記得那張戰報。
雨夜。側翼突擊。敵旗斷裂。
她偷偷把那頁剪下來,夾進自己的詩集。
她曾在燭光下,一遍遍讀他的名字。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
那是帝國的榮耀。
士兵的希望。
也是她少女心中無聲的崇拜。
她甚至幻想過——
若有一日,戰場安定,功勳卓著的將軍或許會進入上層貴族社交圈。
或許在某次宴會上,她能遠遠看他一眼。
哪怕只是行一個禮。
她從未奢望更多。
那樣的人,本就不屬於她這樣的伯爵家。
可是現在——
她慢慢轉過頭。
視線穿過人群。
落在瑪德琳的車前。
四名人馬站在那裡。
最前方的那一人——
肩線沉穩。
頸項微垂。
背脊筆直。
即使佩戴著頸環,即使繩索纏身——
那股氣質依舊無法被壓低。
她的呼吸亂了一瞬。
「他……為什麼……」
侍女低聲回答:
「據說……是公爵親自安排。」
她沒有再問。
因為她知道答案。
為了那位克萊蒙家的大小姐。
為了讓她在人馬大賽中不至於受傷。
為了讓她穩穩站在御車之上。
帝國最鋒利的劍,被卸下軍銜。
帝國最穩的防線,被套上繩索。
成為——
她的馬。
羅蘭伯爵小姐的雙手幾乎失去血色。
她緊緊握住裙子。
不是因為嫉妒。
也不是因為羞辱。
而是一種更複雜、更難以啟齒的情緒。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自己剛才還在為「注定是配角」而苦澀。
可原來——
真正甘願成為配角的人,是他。
為了一個少女。
為了站在她腳下。
為了讓她不必顛簸。
她的胸口發緊。
她甚至不知道該憤怒誰。
是克萊蒙公爵?
是那位小姐?
還是他自己?
她看見瑪德琳站在車上,金髮在風中微揚。
笑容明亮。
她的鞭子在陽光下閃光。
她或許根本不知道自己腳下那人的名字。
不知道他曾在邊境撐住帝國的夜。
不知道多少士兵因他而活。
她只知道——
那匹馬很好。
很穩。
很好看。
羅蘭伯爵小姐的喉嚨發疼。
她忽然意識到——
若比賽開始,若她的紅方在彎月角與克萊蒙家的車並行——
她的鞭子,可能會落在他身上。
干擾。
逼迫。
為了勝利。
為了家族。
她的手輕輕顫了一下。
「小姐?」
侍女輕聲喚她。
她深吸一口氣。
背脊重新挺直。
她不能失態。
不能在王女面前失去鎮定。
不能在公爵小姐面前顯露軟弱。
她抬起下巴。
目光變得冷靜。
但那份冷靜之下,是一道無聲的裂痕。
帝國的榮耀。
士兵的希望。
她心中暗暗愛慕之人。
如今在敵方繩索前端。
而她——
即將揮鞭。
銅管的尾音在黑石之環上空緩緩散去。
塵土落定。
紅旗、白旗、藍旗與翡翠旗垂落在微風裡,像是剛經歷過一場不見血的戰役。
御車依序停下。
侍從迅速上前,擺放踏階——
那踏階不是木製的。
而是人。
四名奴隸伏地,背脊貼著石道,額頭抵地,成為小姐們下車的第一道階梯。
羅蘭伯爵小姐深吸一口氣,穩穩站住。
她的雙腿因緊繃微微發軟,卻沒有讓任何人看出來。
她抬起裙襬,優雅地踏上第一個背脊。
柔軟卻結實。
那是一種她已經熟悉的觸感。
高跟鞋落下。
沒有猶豫。
她走下御車。
紅旗落在她身後,彷彿替她披上一層殘餘的火光。
她得了第四名。
亞軍是——
瑪德琳·德·克萊蒙。
而冠軍,毫無意外,是那位白旗之下的第一公主,夏洛特殿下。
即使是瑪德琳,也不得不在最後一圈,讓出那條內線。
王族的勝利,不需要宣告。
那是默契。
也是秩序。
羅蘭伯爵小姐整理好裙襬,臉上浮現出完美無瑕的笑容。
她主動走向瑪德琳。
「恭賀妳,克萊蒙小姐。」
她的聲音柔軟,甜美,沒有半分尖銳。
瑪德琳回過頭。
金髮微揚,額前還殘留奔跑後的紅暈。
她笑得那麼甜。
那笑容幾乎能把人融化。
「謝謝妳,羅蘭小姐。」
語氣真誠得近乎無辜。
——若不是她剛才在第六圈的彎月角對自己的奴隸下了死手。
若不是那幾鞭抽得毫不留情,逼得那人用肩膀硬頂住車架。
羅蘭幾乎真的會被這張臉騙過。
她伸出手。
瑪德琳也伸出手。
兩人的指尖在空中相觸。
羅蘭握住她的小手。
那手指光滑、溫潤、帶著淡淡的香氣。
沒有一絲粗糙。
沒有一絲顫抖。
她忽然想起——
就在幾分鐘前,這雙手握著鋼絲牛筋纏繞的長鞭。
毫不遲疑。
毫不猶豫。
她的目光緩緩下移。
落在瑪德琳的御車前方。
那裡——
一個身影倒在地上。
繩索還未解開。
背部布滿深淺不一的鞭痕。
胸膛劇烈起伏。
呼吸沉重而急促。
那是——
羅蘭。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
帝國的榮耀。
士兵的希望。
她心中暗暗愛慕之人。
他撐了七圈。
七圈。
沒有替換。
沒有倒下。
直到終點旗落下。
現在,他躺在黑石之上,大口喘氣。
汗水順著鬢角滑落,與血水混在一起。
她的指尖幾乎微不可察地顫了一下。
她輕聲問:
「克萊蒙小姐。」
語氣依舊溫柔。
「那名奴隸……叫什麼名字?」
她期待聽到——
羅蘭大人。
哪怕只是象徵性地保留一點尊稱。
畢竟他是帝國的英雄。
畢竟他的名字曾寫在軍報上。
瑪德琳眨了眨眼。
像是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地上那個人。
她轉過身。
裙擺輕輕劃過空氣。
然後——
毫無預兆地。
她一腳踩在他的臉上。
鞋底壓下。
細長的鞋跟落在他顴骨旁。
羅蘭沒有動。
沒有躲。
只是呼吸更加急促。
瑪德琳笑盈盈地低下頭。
「羅蘭小姐問你叫什麼名字?」
語氣甜得像午後陽光。
地上的男人喘著氣。
喉嚨發乾。
卻仍然清晰地回答:
「……羅蘭。」
那個名字落地的瞬間。
羅蘭伯爵小姐的心臟狠狠一縮。
瑪德琳的笑容——
忽然冷了。
不是失態。
不是暴怒。
而是一種極其輕微、卻清晰可見的寒意。
「羅蘭?」
她微微歪頭。
鞋底輕輕碾了一下。
「一名奴隸……怎麼能和羅蘭小姐同名?」
語氣仍然溫柔。
卻帶著不容置疑的界線。
她抬起腳。
鞋跟在他臉上留下一道紅痕。
「從今天起,你改名。」
她淡淡地說。
「別再用這個名字。」
羅蘭伯爵小姐的笑容沒有消失。
她仍然站得優雅。
仍然保持著甜美的弧度。
但她的指甲,已經深深掐進掌心。
那個名字。
曾是戰場上的傳說。
現在——
被踩在鞋底下。
而她什麼都不能說。
紅方——羅蘭伯爵小姐
賽場中央,深紅色的大旗在湖風中獵獵作響。
那不是明亮的紅。
而是近乎酒色的深紅——厚重、濃烈,像歷史沉澱後的血與榮耀。
羅蘭伯爵小姐站在御車之上,指尖微微收緊。
她的裙裝以紅絲緞為底,邊緣以黑金細線繡出家族的狼紋徽章。狼頭低伏,目光銳利——象徵她們家族自北境荒原崛起的歷史。
紅寶石耳墜隨風輕晃,映著陽光,折射出微小卻鋒利的光點。
她的姿態優雅,背脊筆直,肩線穩定。
從看台遠望,沒有人能察覺她此刻心底翻湧的情緒。
在這場人馬大賽中,她既沒有克萊蒙公國那樣的底蘊,也沒有西勒斯公國那樣的商業傳承。
更何況——
那一位。
皇帝第一公主——夏洛特殿下。
羅蘭伯爵小姐輕輕吐出一口氣。
她不是天真少女。
她很清楚這場比賽真正比拼的是什麼。
不是速度。
不是技巧。
而是——背後的力量。
她的父親,羅蘭伯爵,領地廣闊,邊境穩固,家族歷史超過三百年。
在地方議會中,他說話仍有分量。
在北境,他的軍隊仍然令人敬畏。
但在聖蘭諾學院這樣的舞台——
公爵與王族的陰影太過巨大。
伯爵府的書房燭火搖曳。
父親站在窗前,背對著她。
「紅方不好跑。」他低聲說。
她沒有回答。
「我們準備了三組牽引。」
「第一組是舊軍士,穩。」
「第二組是你叔父親自挑的,爆發力強。」
「第三組……」他停了一下,「……他們撐不了太久,但夠拼命。」
她知道那句話的意思。
夠拼命。
在這場賽事裡,那意味著什麼,她比誰都清楚。
她沒有哭,也沒有抱怨。
只是輕聲說:「我會讓他們跑得值得。」
那一瞬間,她看見父親眼裡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驕傲。
擔憂。
還有無法言說的現實。
因為他知道——
她注定不是這場盛宴的主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賽場上,四組人馬已就位。
紅方的第一組站在她腳下。
四名男人,肩寬背闊,腰部束帶繃緊。
他們的皮膚因長年軍旅而略帶粗糙,肌肉線條清晰。
其中兩人臉上仍留有舊戰傷的痕跡。
她認得他們。
那是父親舊部。
他們曾在邊境守夜,曾為家族擋過流箭。
如今,他們低頭站在她面前,頸環在陽光下泛著金屬光澤。
她的喉嚨微微發緊。
她必須駕馭他們。
否則,他們的犧牲只會成為笑話。
紅旗在風中翻動。
她抬起手,白手套包覆著纖細的手指。
長鞭在陽光下閃過一抹冷光。
她並不喜歡鞭子。
她練習過很多次。
但每一次落下,手腕都會不自覺遲疑。
不像公爵家的小姐們,那樣自然。
不像王女那樣毫無動搖。
她知道自己會是配角。
這時,一道極輕的腳步聲自車後傳來。
她的侍女——莉亞——靠近一步,俯身,聲音幾乎被風吞沒。
「小姐……」
她沒有回頭,只是微微側耳。
「克萊蒙家的頭馬……」
莉亞停了一下,像在斟酌用詞。
「是羅蘭大人。」
風忽然變得很冷。
她的指尖猛地收緊。
絲緞被捏出一道深深的摺痕。
「……哪位羅蘭?」
她的聲音仍舊平穩。
侍女的喉嚨滾動了一下。
「瓦爾克羅瓦大人。」
那一瞬間,賽場的聲音彷彿全部遠去。
銅管聲、學生低語、旗幟翻動——
全部被抽離。
她聽見的只有自己的心跳。
羅蘭。
那個名字,對她而言,從來不是普通的軍報字眼。
她年幼時曾站在父親書房外,偷聽將軍們談話。
那個名字反覆出現——
「只要瓦爾克羅瓦還站著,戰線就不會崩。」
她記得那張戰報。
雨夜。側翼突擊。敵旗斷裂。
她偷偷把那頁剪下來,夾進自己的詩集。
她曾在燭光下,一遍遍讀他的名字。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
那是帝國的榮耀。
士兵的希望。
也是她少女心中無聲的崇拜。
她甚至幻想過——
若有一日,戰場安定,功勳卓著的將軍或許會進入上層貴族社交圈。
或許在某次宴會上,她能遠遠看他一眼。
哪怕只是行一個禮。
她從未奢望更多。
那樣的人,本就不屬於她這樣的伯爵家。
可是現在——
她慢慢轉過頭。
視線穿過人群。
落在瑪德琳的車前。
四名人馬站在那裡。
最前方的那一人——
肩線沉穩。
頸項微垂。
背脊筆直。
即使佩戴著頸環,即使繩索纏身——
那股氣質依舊無法被壓低。
她的呼吸亂了一瞬。
「他……為什麼……」
侍女低聲回答:
「據說……是公爵親自安排。」
她沒有再問。
因為她知道答案。
為了那位克萊蒙家的大小姐。
為了讓她在人馬大賽中不至於受傷。
為了讓她穩穩站在御車之上。
帝國最鋒利的劍,被卸下軍銜。
帝國最穩的防線,被套上繩索。
成為——
她的馬。
羅蘭伯爵小姐的雙手幾乎失去血色。
她緊緊握住裙子。
不是因為嫉妒。
也不是因為羞辱。
而是一種更複雜、更難以啟齒的情緒。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自己剛才還在為「注定是配角」而苦澀。
可原來——
真正甘願成為配角的人,是他。
為了一個少女。
為了站在她腳下。
為了讓她不必顛簸。
她的胸口發緊。
她甚至不知道該憤怒誰。
是克萊蒙公爵?
是那位小姐?
還是他自己?
她看見瑪德琳站在車上,金髮在風中微揚。
笑容明亮。
她的鞭子在陽光下閃光。
她或許根本不知道自己腳下那人的名字。
不知道他曾在邊境撐住帝國的夜。
不知道多少士兵因他而活。
她只知道——
那匹馬很好。
很穩。
很好看。
羅蘭伯爵小姐的喉嚨發疼。
她忽然意識到——
若比賽開始,若她的紅方在彎月角與克萊蒙家的車並行——
她的鞭子,可能會落在他身上。
干擾。
逼迫。
為了勝利。
為了家族。
她的手輕輕顫了一下。
「小姐?」
侍女輕聲喚她。
她深吸一口氣。
背脊重新挺直。
她不能失態。
不能在王女面前失去鎮定。
不能在公爵小姐面前顯露軟弱。
她抬起下巴。
目光變得冷靜。
但那份冷靜之下,是一道無聲的裂痕。
帝國的榮耀。
士兵的希望。
她心中暗暗愛慕之人。
如今在敵方繩索前端。
而她——
即將揮鞭。
銅管的尾音在黑石之環上空緩緩散去。
塵土落定。
紅旗、白旗、藍旗與翡翠旗垂落在微風裡,像是剛經歷過一場不見血的戰役。
御車依序停下。
侍從迅速上前,擺放踏階——
那踏階不是木製的。
而是人。
四名奴隸伏地,背脊貼著石道,額頭抵地,成為小姐們下車的第一道階梯。
羅蘭伯爵小姐深吸一口氣,穩穩站住。
她的雙腿因緊繃微微發軟,卻沒有讓任何人看出來。
她抬起裙襬,優雅地踏上第一個背脊。
柔軟卻結實。
那是一種她已經熟悉的觸感。
高跟鞋落下。
沒有猶豫。
她走下御車。
紅旗落在她身後,彷彿替她披上一層殘餘的火光。
她得了第四名。
亞軍是——
瑪德琳·德·克萊蒙。
而冠軍,毫無意外,是那位白旗之下的第一公主,夏洛特殿下。
即使是瑪德琳,也不得不在最後一圈,讓出那條內線。
王族的勝利,不需要宣告。
那是默契。
也是秩序。
羅蘭伯爵小姐整理好裙襬,臉上浮現出完美無瑕的笑容。
她主動走向瑪德琳。
「恭賀妳,克萊蒙小姐。」
她的聲音柔軟,甜美,沒有半分尖銳。
瑪德琳回過頭。
金髮微揚,額前還殘留奔跑後的紅暈。
她笑得那麼甜。
那笑容幾乎能把人融化。
「謝謝妳,羅蘭小姐。」
語氣真誠得近乎無辜。
——若不是她剛才在第六圈的彎月角對自己的奴隸下了死手。
若不是那幾鞭抽得毫不留情,逼得那人用肩膀硬頂住車架。
羅蘭幾乎真的會被這張臉騙過。
她伸出手。
瑪德琳也伸出手。
兩人的指尖在空中相觸。
羅蘭握住她的小手。
那手指光滑、溫潤、帶著淡淡的香氣。
沒有一絲粗糙。
沒有一絲顫抖。
她忽然想起——
就在幾分鐘前,這雙手握著鋼絲牛筋纏繞的長鞭。
毫不遲疑。
毫不猶豫。
她的目光緩緩下移。
落在瑪德琳的御車前方。
那裡——
一個身影倒在地上。
繩索還未解開。
背部布滿深淺不一的鞭痕。
胸膛劇烈起伏。
呼吸沉重而急促。
那是——
羅蘭。
羅蘭·德·瓦爾克羅瓦。
帝國的榮耀。
士兵的希望。
她心中暗暗愛慕之人。
他撐了七圈。
七圈。
沒有替換。
沒有倒下。
直到終點旗落下。
現在,他躺在黑石之上,大口喘氣。
汗水順著鬢角滑落,與血水混在一起。
她的指尖幾乎微不可察地顫了一下。
她輕聲問:
「克萊蒙小姐。」
語氣依舊溫柔。
「那名奴隸……叫什麼名字?」
她期待聽到——
羅蘭大人。
哪怕只是象徵性地保留一點尊稱。
畢竟他是帝國的英雄。
畢竟他的名字曾寫在軍報上。
瑪德琳眨了眨眼。
像是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地上那個人。
她轉過身。
裙擺輕輕劃過空氣。
然後——
毫無預兆地。
她一腳踩在他的臉上。
鞋底壓下。
細長的鞋跟落在他顴骨旁。
羅蘭沒有動。
沒有躲。
只是呼吸更加急促。
瑪德琳笑盈盈地低下頭。
「羅蘭小姐問你叫什麼名字?」
語氣甜得像午後陽光。
地上的男人喘著氣。
喉嚨發乾。
卻仍然清晰地回答:
「……羅蘭。」
那個名字落地的瞬間。
羅蘭伯爵小姐的心臟狠狠一縮。
瑪德琳的笑容——
忽然冷了。
不是失態。
不是暴怒。
而是一種極其輕微、卻清晰可見的寒意。
「羅蘭?」
她微微歪頭。
鞋底輕輕碾了一下。
「一名奴隸……怎麼能和羅蘭小姐同名?」
語氣仍然溫柔。
卻帶著不容置疑的界線。
她抬起腳。
鞋跟在他臉上留下一道紅痕。
「從今天起,你改名。」
她淡淡地說。
「別再用這個名字。」
羅蘭伯爵小姐的笑容沒有消失。
她仍然站得優雅。
仍然保持著甜美的弧度。
但她的指甲,已經深深掐進掌心。
那個名字。
曾是戰場上的傳說。
現在——
被踩在鞋底下。
而她什麼都不能說。